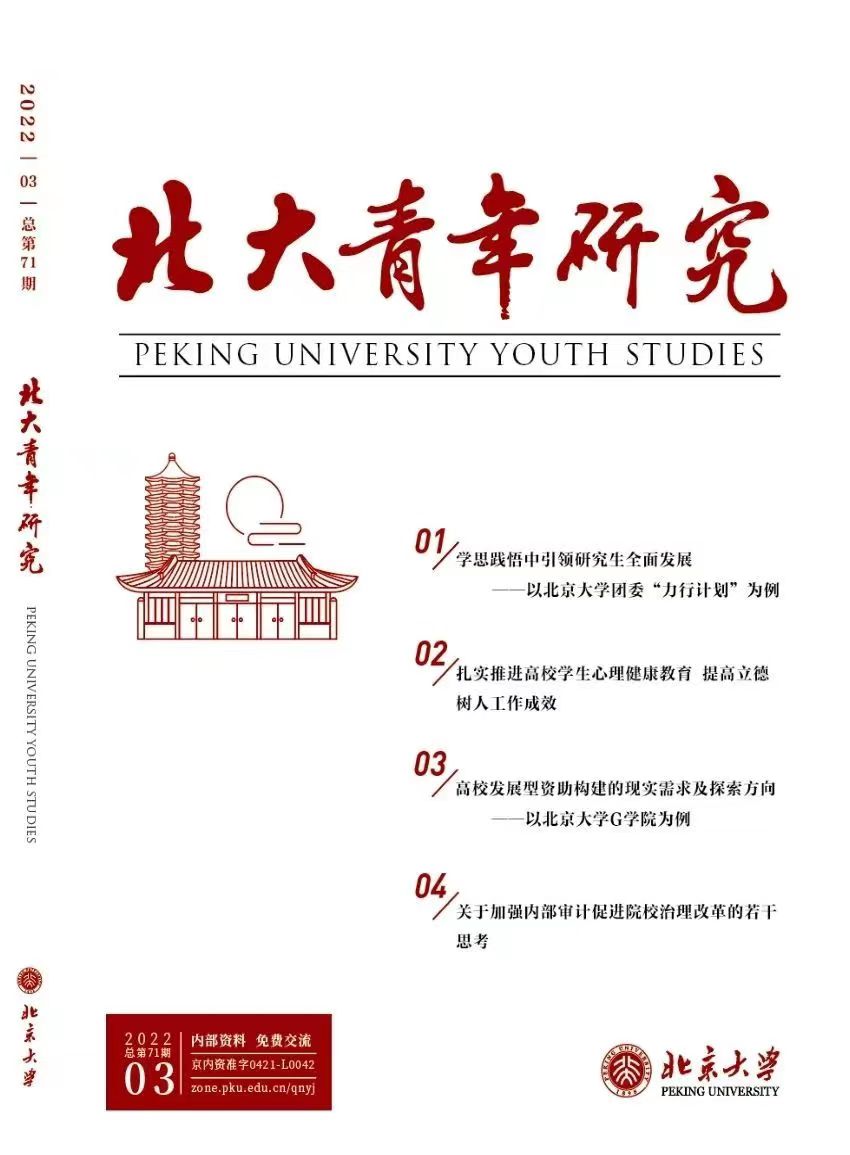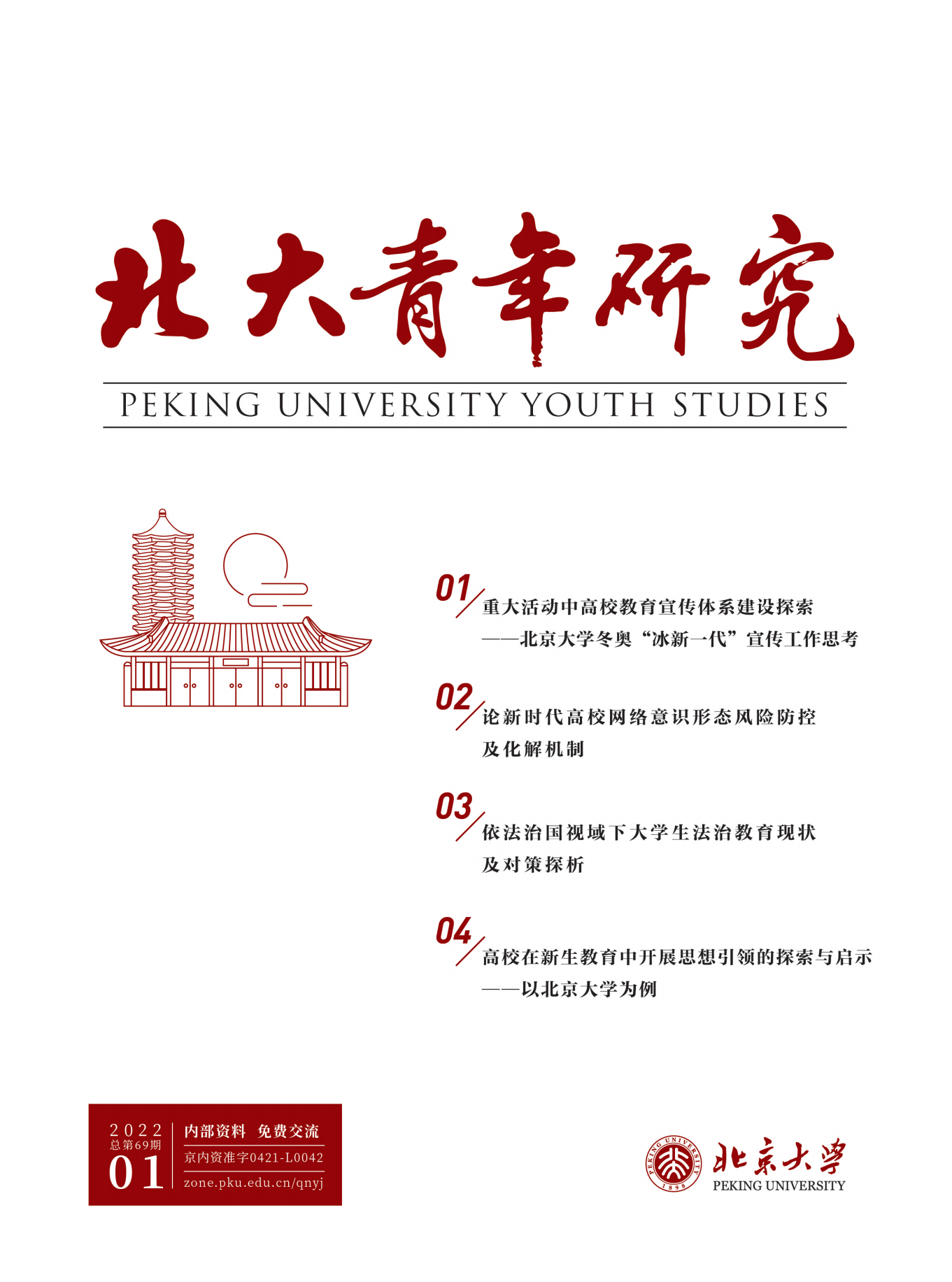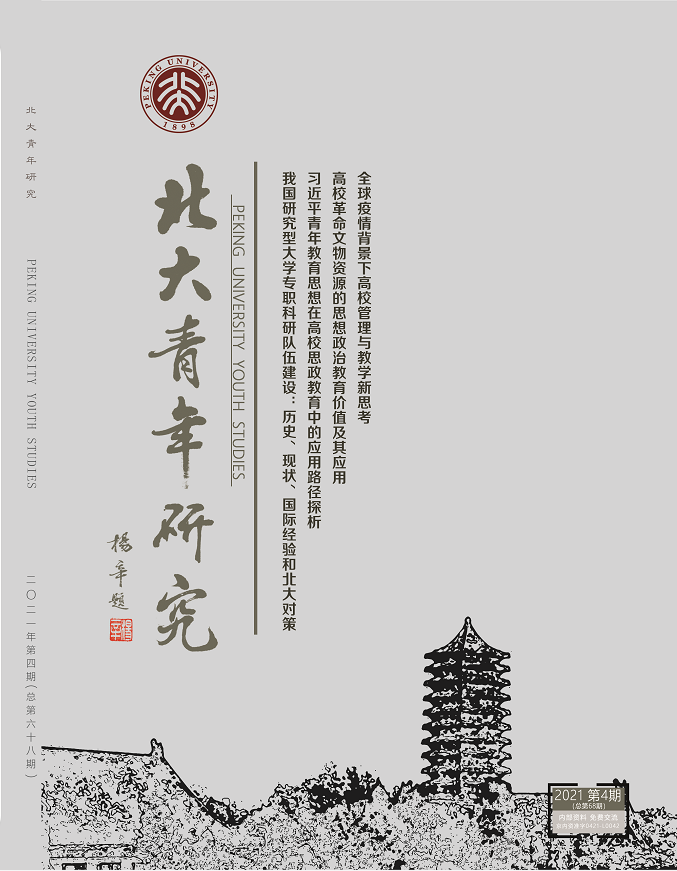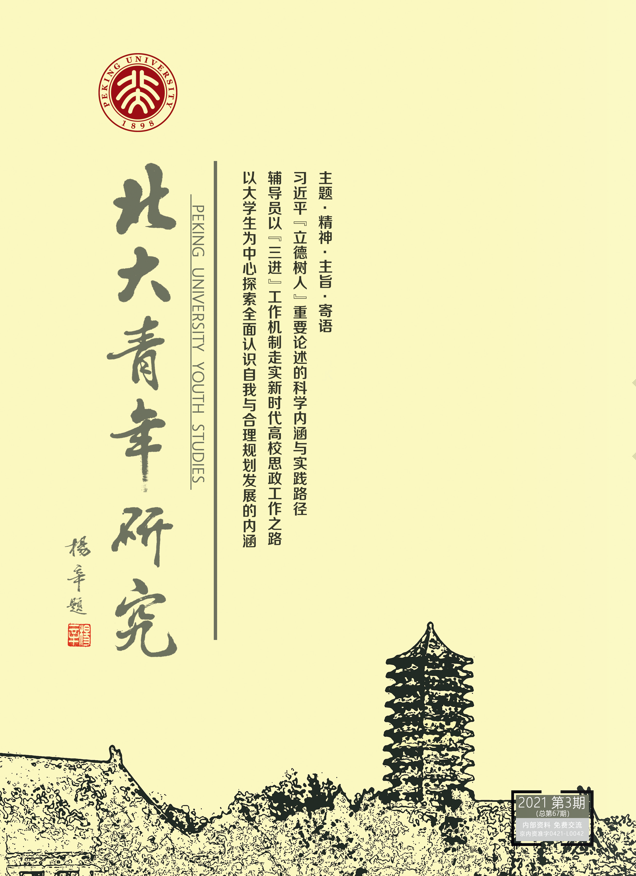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为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我们还只是树上猿猴时,动物和致病微生物的战争便已持续了亿年。在这之后的短短百万年时间内,人类族群穿过了食物链的无尽黑暗,走出丛林,最终围坐在文明的火堆边,有了部落,有了城邦,有了共和国,但那些同样绵延数亿年的疾病“朋友”们却也从未离开。2020年,身处能够更好地聚集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现代文明丛林,很多人第一次如此紧迫地认识到“传染病”三个字的可怕。理解现代都市与生活,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与各国疫情对策的核心逻辑。
一、现代城市与传染病
“集中”塑造了现代城市,局部的集中催生了现代的城际交通运输体系。“大聚集”与“快流动”成为了现代的关键特征。得益于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瘟疫在这一阶段才浮出水面。
城市首先是集中。人类历史长河中,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居民只占据了很小的比例。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空前高速的城市化之后,目前,全世界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工业革命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所产生的供需双方强大驱动力下应运而生。蒸汽、煤炭、污浊的空气、电气、自来水、下水管道,城市代表了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
城市同时需要流动。生产不同工业产品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工厂与原材料产地之间,城市与作为城市食物供给地的周边农村之间,城市内生活区与工商业区之间,工业原料、产品与劳动力,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要义是流动。城市在快速集中资源的同时,也将依赖更大的流动性以维持其资源需求、城市运转。人的交通,物的运输,信息传递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加快了城市的形成,也成为了维系城市的基础。最终,集中度、流动性也成为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基石。
但,传染病的扩大蔓延,恰恰离不开这两点。
古代农业社会或是游牧部落,人口分散、流动速率缓慢,瘟疫还未能真正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一场大瘟疫的形成和蔓延往往需要前后上百年的时间。它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屠尽一个又一个部落与村庄,也因为过快地消灭了人类宿主而很难继续传播下去。但其中也存一些特例,比如鼠疫,因为依靠老鼠、跳蚤等常见的动物媒介传播,更容易打破农业社会的低速传染模式,成为了东西方共同的灾难记忆。如今,在全球超级城市群与洲际航班的双重加持下,新冠肺炎病毒这类可在人类间传播的强传染性疾病的威力,得以充分展现。
城市的人口集聚,城市间的人口快速流动,让我们在享受了技术资本人口密集的快速发展红利的同时,也等比例地放大了疾病、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地球村里的你我他由此命运相连。
中国的现代城市系统,则体现为更加复杂的城乡间周期性的聚集—流动模式。中国的东部沿海、内地关键航运节点的城市吸引了大批来自农村与次一级城市的劳动力。他们类似周期性的潮汐,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工作地与家乡之间。而春运,就是其中的“钱塘大潮”。当春运遭遇疫情,兼具城乡间人口快速流动、公共交通方式密集运转的双重挑战的中国,拿到的是全世界最难的试题。
二、现代城市的医疗资源:充足与不足
医学与人类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医疗产业的特殊性质。
首先,现代医学在科学革命中诞生,人类对自身的机体、疾病的认识得到了极大丰富,医疗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人类整体的健康水平相较前代得到了极大提高。然而,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手工业”。下此定义的出发点在于,如果把医疗看作一种“生产”,这种“生产”的短缺关键在于作为核心要素的医护人员群体是不可量产的。换而言之,人类可以享用烹饪机器人做出的饭菜,可以想象无人驾驶技术的加速到来,甚至可以阅读写作软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但却很难接受为你做手术的是一个机器人。这就意味着,医疗的核心“软件”资源数量不能实现工业化制造领域产生的相对过剩状态,也无法充分满足工业社会日益高涨的健康需求。这也同时意味着现有的“软件”存量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应对城市化、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挑战。
相对丰富与相对短缺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以中国为观察对象,试图分析一下从武汉爆发到全国疫情逐渐平稳,我们切切实实地跨过的三种短缺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首先出现的第一种短缺,是短期的诊疗资源短缺,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分诊分流过程的医疗系统在传染病爆发状态下的短期挤兑。这极大提高院内感染的风险。
自古代以来,具有厚生主义传统的中国政府便非常重视人民的健康水平。尽管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我国依旧坚持以公立医疗设施为主体,坚持普惠医疗理念,以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追求高质量健康生活的中国百姓习惯了不管生病大小,都往为数不多的三甲医院跑。在缺乏分级诊疗的系统中,大量病人并不习惯小病在家服药治疗。有病没病、大病小病,医院看病是常态。而此次疫情爆发恰逢冬春两季的流感季节,各大医院中已经塞满了大量因普通呼吸道感染而前往就诊的病人。在传染病来临后,武汉各大医院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有发热、咳嗽症状的患者。这其中既有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者,亦不乏大量普通病患者。这样的“混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的扩散。因此,在传染病疫情防控初期出现的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主要是由医疗分诊体系的不健全和恐慌带来的医院挤兑等造成的。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短缺在中国抗疫历程中只是软性的、短期的,随着分诊机制的不断规范和完善而缓解。尤其体现在大量医疗资源被集中投入以及诊断标准的重大调整(例如,核酸检测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影像判据纳入核准依据)。患者在诊断和简单治疗给药环节更加高效,在隔离举措更加及时且彻底的情况下,交叉感染的概率在明显降低,医院挤兑现象造成的医疗资源紧张也会缓解。
第二种短缺是刚性的、长期的短缺,表现为重症、危重症救治资源的严重不足。如果仅仅从死亡率与病重率的统计数字上看,我们很容易低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即使是医疗资源更丰富、分诊制度更严密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面前也彻底“颜面无存”。只有5%的重病率,已经使各国现有的重症治疗体系遭受了一次巨大冲击乃至打击。
英国皇家联合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顾问蒂姆库克(Tim Cook)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目前预计英国全境将有30%以上的人口感染新冠肺炎;根据某些预测,这个数字或将达到60%。大部分感染者将无症状或出现轻微症状,有1/7的人会需要入院治疗。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中1/5的人可能需要ICU监护,这将是前所未见的惊人数字,而每50位患者中可能会有1位死亡病例,而全英只能提供4100个床位。”
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英国,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我们可以对全世界的重症监护体系有更清醒的认识。数据表明,虽然优质医疗资源更加集中分布在大型城市内,但即使在美国,相比重症发病率,人均ICU等重症监护资源也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由此带来的人伦悲剧是,当某个国家的感染比例达到一定数值时,可能将有数十万人不是在被拯救后死于“恶性疾病”,而是在被拯救前死于“资源短缺”。
这样的短缺是刚性的、长期的。库克医生同时表示,2017年英国大部分ICU床位的使用率也已经达到了90%甚至更高。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治疗将快速挤占各国本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大病的宝贵的医疗资源。
简而言之,现代城市现有的重症医疗资源,在几乎所有具备高度传染性的大型传染疾病已处于高度爆发期时,根本无法、也无力应对。
第三种短缺引发了更为深层次的关于工业生产等话题的思考,表现为复杂的医疗器械产业链、医生资源的长期打击。如前文所述,ICU中急需的设备设施在各国面对大规模疫情爆发时,都会出现匮乏的现状。那么短期内加快生产、增加供给是否可能呢?现实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抗疫初期,口罩、酒精消毒液一类的基础防护用品都出现了大量缺口。而影响生产最重要的就是生产线、员工、原料的紧缺问题。即使是五菱汽车这样具备大型生产流水线、大规模高级工程师团队的一流制造企业,开辟一个口罩生产线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在疫情爆发时,晚一小时都将给民众心理带来极大恐慌。
显而易见,呼吸机、ECMO等专业设备的生产难度更是巨大。在面临流水线扩容、工厂雇员减少、全球物流阻塞、亚洲上游原料产地减产等一系列问题时,也将更加脆弱。事实也清楚地表明,当传染病疫情全面扩大后,全球范围内的短期国际医疗资源供给将异常困难,希望通过增加医疗资源扩容挽救生命的尝试注定艰难。
更为可怕的是,防护设备的短缺,最终造成医疗流程中最难以补充、也最核心的资源——医务工作者——遭受最大的打击。这样的减损难以逆转。
面对医疗资源长期以来低存量、短期难以增加供给的现状,难道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人类该如何解决已经扩散出现的强传染疾病在现代城市中的蔓延呢?
三、对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
首先,应该意识到,“在瘟疫面前,无论何族何地,苦难都不容戏谑,努力该被看见”,共同战斗的世界人民付出的泪与汗换来的经验与教训、疏忽与警醒、反思与哀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永恒的记忆。深入、科学地检视现有的成功“模式”与正在进行的“方案”,血肉之痛,不容扭曲。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下的疫情防控效果是显著并富有成效的。中国第一个成功地控制住了国内疫情,这样的阶段性胜利,不容置疑。在这里,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而不只是“中国方案”,表达的就是对其效果的肯定。
理解“中国模式”,需要先理解其运行机制。在防控逻辑上,其表现为“防扩散”“治重症”的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在具体行动上,主要表现为城市管制、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为代表的“三板斧”。
理解“中国模式”,需要复盘中国的防疫措施。正式开始执行“封城”时,武汉市内的病例已经大量存在并向市外输出,传染进入病例指数快速上升期。于此同时,春运在即,“九省通衢”的武汉,人员的流动性、交通工具狭小空间中的密集性使得传播的风险大幅度升高。封城、全国阻断交通,是此时的必要举措。需要指出的是,封城并不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也不是理解“中国模式”与中国国家特点的关键。我们应该看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疫情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别,阻止传播拥有防止疫情扩散的最高优先级,但现代城市运行所需的资源巨大且复杂,在未谨慎考虑物资供给的状况下贸然封城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损失与浪费。
理解“中国模式”,必须从现代城市与传染病防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入手。“中国模式”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挽救更多的生命,核心逻辑在于“集中”的集体主义防疫策略。如前文所述,在面临高强传染性疾病时,医疗资源存在的供给与需求间巨大缺口客观存在,这是现代城市与传染病防治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模式”的“集中”与现代城市的“集中”内生逻辑是相通的。这种“集中”体现在全国抽调大批重症医疗资源、护理资源集中投放疫区,通过最大密度的医疗资源输血,实现资源集中,防止疫情在关键、严重地区出现继续扩散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治疗重症、降低死亡,并及时支持因工作暴露而有更大风险的当地一线医护人员。
中国抗疫时间轴上的一个重要日期是2020年1月24日。从这天起,包括军队在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逆行而上,奔赴湖北。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截至3月8日,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6万人抵达武汉和湖北,其中重症专业医务人员1.9万。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都是这一群逆行者的战场之一。
近4个月过去后的5月21日,当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破5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3万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在这一语境下的深刻含义。所谓“集中力量”,就是在疫情已经全面爆发的状态下,分清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办“大事”,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这样的头等大事。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关切,是中国体制在疫情关键时期凸显的最大制度优势。放眼全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拥有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有计划地社会动员、跨域资源调配、统筹协调能力。
诚然,“中国模式”并不代表中国抗疫是完美无缺的,并不代表要用肯定来掩盖问题。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在这这样一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愿意轻易触及的资源无底洞面前,我们期待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理想中的道路是什么?面对每一条生命还是每一分债务代价的艰难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伟大豪迈有悲壮,有的冰冷无奈仍彷徨。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庞大社会运动中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在家中配合守候的全国人民,都是“中国模式”的关键,也是“中国模式”的独特之根本所在。这份“作业”从来不是人人都能抄、人人都看得明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当代集体主义最直接的体现,在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精神、伦理道理观念里,有“中国模式”最闪耀的精神魅力。
当传染病出现时,各国应对方式的不同确实有基于政治文化传统差异的因素,但一切差异都应该是以维护国民生命安全为底线的。不理解这个前提,所谓的“不同”或者“不对”都是空洞的,西方的契约精神和自由的核心价值观亦然。
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各做鸵鸟,只会让我们用两百多年发展的现代医学资源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不自由,毋宁死”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对群体其他成员生命权的直接践踏。错误地理解集体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将其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简单粗暴地对立起来,是当代社会的另一种平庸之恶。
作者简介:余鸿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本科生
谢涵歌、王帅宇、宋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