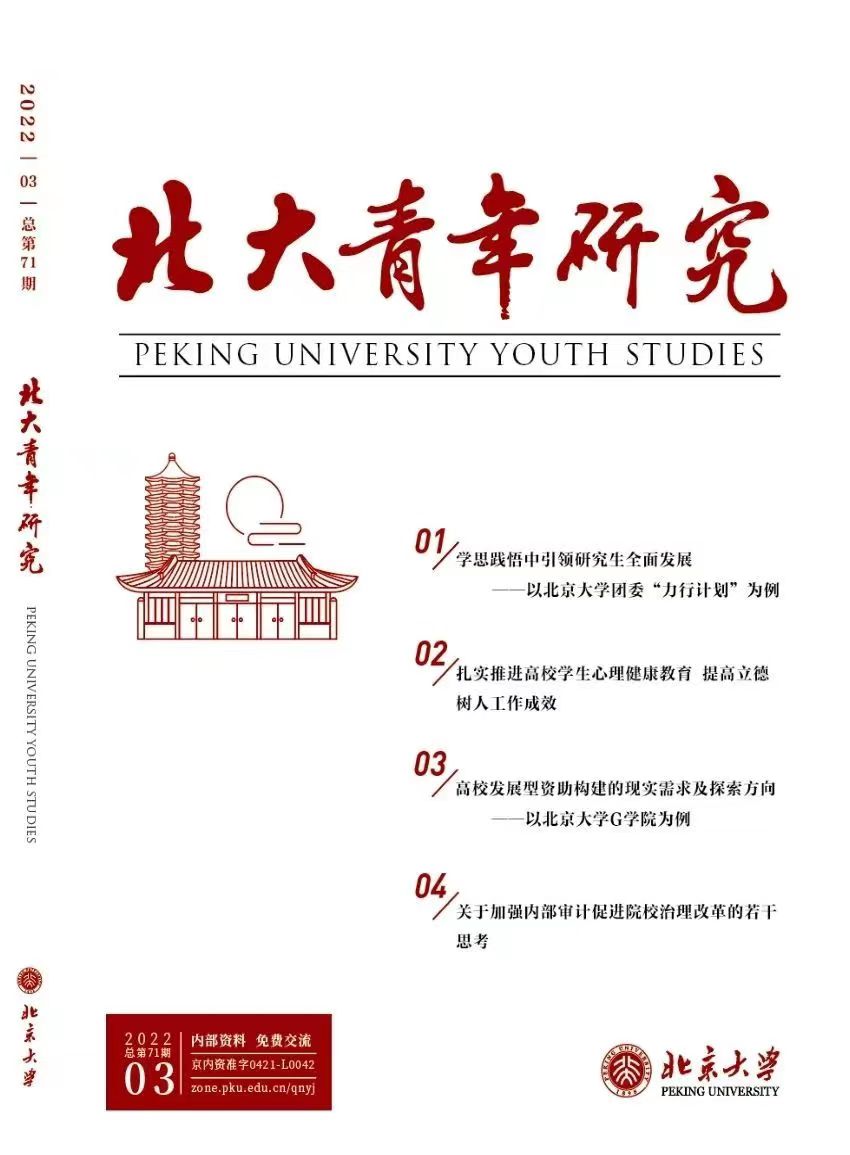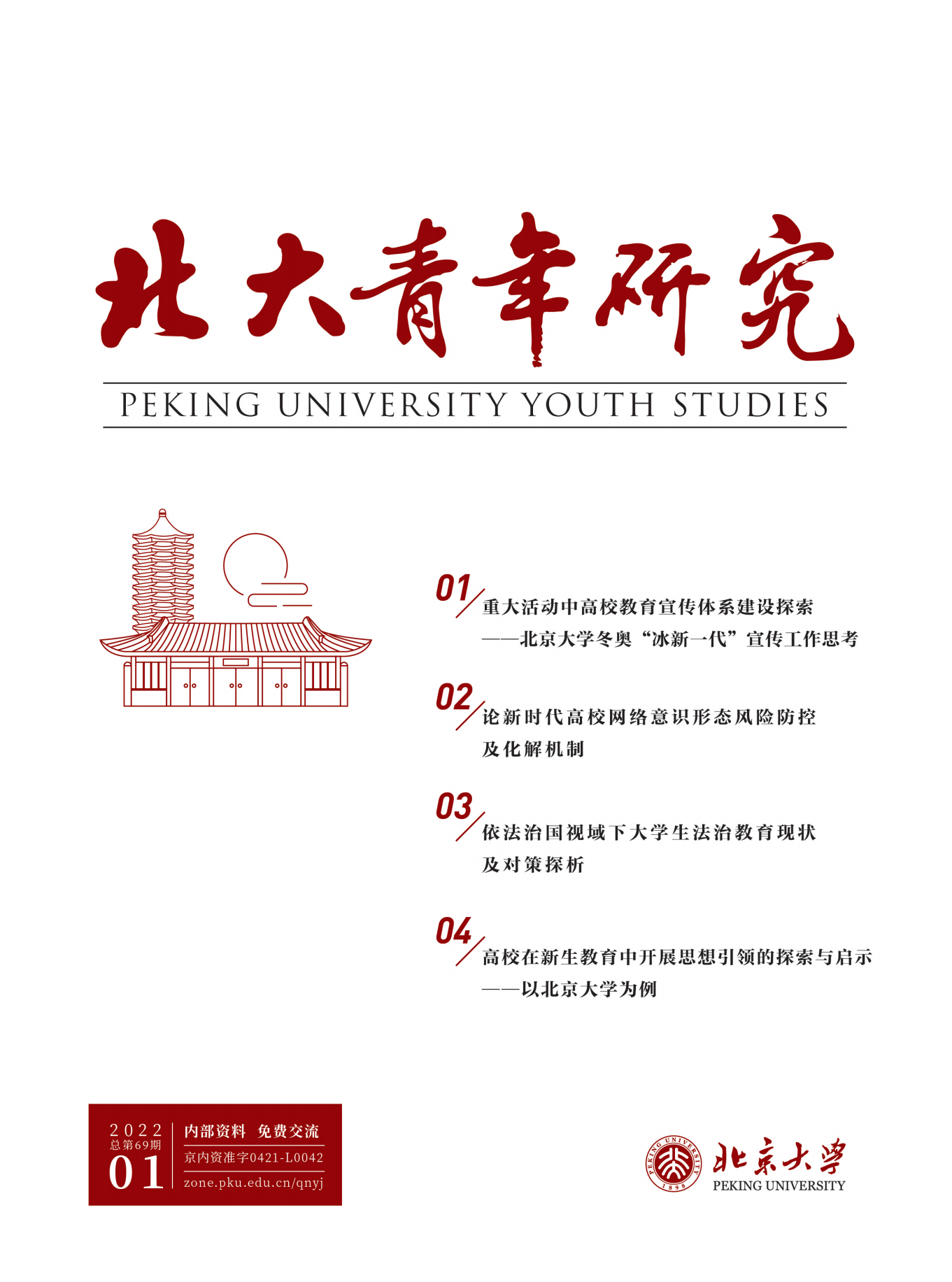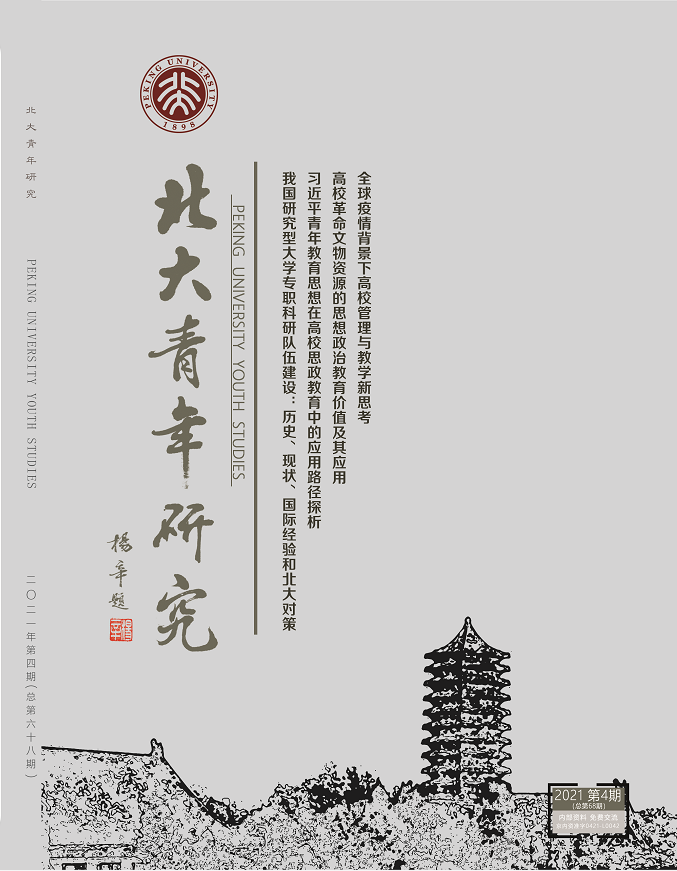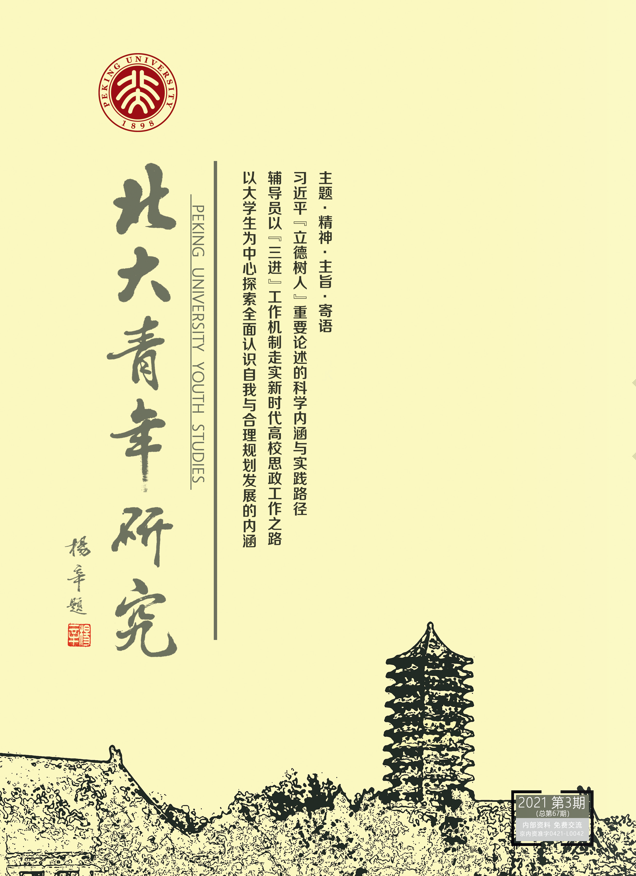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中的后真相迷局 ——兼谈突发流行病时期舆情后真相化的挑战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与应用,新兴媒体得到蓬勃发展,单项传播为主导的传统媒体逐渐没落,多媒介并存的全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在此大环境之下,技术对信息的解构和建构、信息素养的不对称等因素使得人们能够轻易获取的信息多为被“裹挟”的假象,形成了情绪在客观之前、话语在思考之前、成见在事实之前的后真相自由准则,认知的客观性开始让位于主观性。这些变化给现实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在特殊时期更容易扩大负面效应,使之发酵成后真相舆情。文章从后真相的含义出发,分析其在信息传播中带来的问题,并结合突发流行病这一特殊时期探讨舆情后真相化的危害,最后对困境的消解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后真相;全媒体;突发流行病;舆情;挑战
一、后真相的基本含义与特征
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发表剧作家史蒂夫•特希奇在反思伊朗门事件和波斯湾战争时第一次使用“post-truth”这一概念,中文译作“后真相”,2016年11月“后真相”被列入《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它主要由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等争议性爆点新闻而成为热点。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陈述事实真相更能影响舆论”[1],这原本是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的一个热词,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已经远远超越政治领域,在心理认知、新闻传播、经济商业、文化交流等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2],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而这些变化除了引起热度讨论外,对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后真相时代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忽视真相的客观性,真相变得不再重要,“雄辩”胜于“事实”,实际上后真相从情感和信念的角度重构了公众认知。后真相是针对真相而言的,真相指的是事物的本质,由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得知,也是社会共识的基础,追求真相是传统媒体的一项基本准则,人类依托客观固定的外在信息来获取事物的真相。但是随着数字媒介、大众媒体、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信息在技术手段下轻易便能被修改,再借助传播方式的作用力,真相和信息之间的固有联系变得不再明确。加之现代媒体平台进入门槛低、表达图文并茂、交互即时性强的特点,使得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信息世界变得真假难辨,信息能解构真相甚至建构真相,后真相时代也由此诞生。在后真相时代,真相无法主导社会舆论,认知的基础从客观性到主观性逐渐过渡,迥异于传统的从真相达到共识的逻辑,带来舆论幻象和理性坍塌,也侧面反映了精英主义共识和主流价值观念不断遭受质疑的现实。
在后真相时代,公众的个人价值取向变得优先,评判上出现情和理的倒序,有学者用“怨恨”表征后真相所带来的“坏的主观性”[3],用通俗流行的说法就是“有毒的”,彻底的后真相是拒绝交流与共识的,网络交流的秩序化与法制性都会被排斥。
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中面临的后真相问题
(一)消费主义对信息传播取向的干扰
网络时代绕不开资本,消费主义的浪潮下,盈利原则至高无上,资本的逐利性质让流量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尺度,吸引眼球、猎奇性、点击率、关注热度是重点考虑的,而客观与实事求是等原则变得次要甚至不再重要。资本有它固有的市场逻辑,在开放的环境下,各种技术工具,心理操纵技巧,娱乐化方式等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加全面的控制,利益的隐形介入从而左右事实真相,信息内容输出围绕利益关系展开,培养娱乐真相,争占话语权。行业内的竞争也会迫使信息传播在速度上争分夺秒,谨慎求证变得奢侈,人们能够轻易捕捉的信息往往是裹挟后的假象,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增强,后真相可如同病毒式扩散,也为网络空间治理带来难题。
(二)个体的非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影响
个体从网络上冗杂的信息海洋里甄别事实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实在太大,也使得追求真相变得过于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信息的理性化认知会逐渐式微,而较为简单的立场判断和情感选择更容易被接受。科学严谨的论证,长篇大论的分析对大众来说并不“友好”,而情感宣泄、随性批判更能引起“心理舒适”,特别是极端案例的揭露和负面消息的渲染更容易成为舆论场的焦点,促使公众情绪表达和评论的不确定性增强,也让社会心态的培育变得困难重重。
全媒体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性格特征,人们不仅是信息接收方,也是信息传递方和信息生产方。不得不承认,网络中个体的发声几乎都会基于个人的认知与经历,是唯个体行动逻辑的,如果强调对每一份个体声音都要理解就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差异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集体和责任意识容易被忽视,互联网的匿名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网民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世纪,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乌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就论述了社会大众的盲从与偏见,到了后真相时代,更可怕的是真相不再被尊重,追求真相变得落伍和多余,民粹化和反对主流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三)新技术带来的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等困境
“信息茧房”指的是大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自身需求并不全面,容易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能使自己产生愉悦感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就容易陷入一个茧房般的封闭区域,对自己关注点之外的区域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回声室效应跟“茧房”也有类似的特点,人处在较为封闭的空间里,类似的信息和看法在个体的身边反复出现,那么他会更加认定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的看法占据主流,即便他们关注的信息是虚假的也很难被纠偏[4]。
凭借交互自主性、即时参与性等优势,新媒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和传播的主要媒介,同时也为公众情绪宣泄提供了平台,而这种平台多为部落化的小圈子,只欢迎“圈内人”,形成固定社群和圈层,对“异见”的排斥性很强。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信息不断涌现,加上算法推荐系统等技术通过用户偏好的选择,对网络内容进行过滤性推送,个体的信息接受不再是无限制的均质过程,自我推断的片面信息会反复出现,且这种偏置难以逆转,就会形成信息遮蔽,也为后真相提供了生存空间。
三、突发流行病时期舆情后真相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后真相现象源于西方异常政治现象,我国有关后真相的探讨则有所不同,并不是在政治事件上彰显,而是在社会公共话题容易爆发讨论,2018年以来舆情后真相化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网民更关心社会公共事件,尤其是公共卫生类事件[5]。本段基于本土化色彩,结合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现实,对突发流行病这一特殊时期舆情后真相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情感宣泄的支线干扰应对时艰的主线
突发流行病很像遭遇战,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猝不及防,即没有准备,一时间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各种问题会不断爆发。其中夹杂着情绪的UGC内容,成为谣言、极端观点滋生的沃土,此时情绪如同“社会货币”一般成为可调动的社会资源。看过《奇葩说》这一辩论综艺的观众可能发现,辩手们自己都会承认讲故事、挑情绪是取胜的手段,它不像法庭辩论,诉诸于摆事实、讲证据,反而深谙情绪调动能获得更多支持的现象,这时候辩手们就极容易陷入诡辩。但突发流行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它不是一场可以不去消除分歧的辩论,而是迫切地需要去解决实际问题,此时情绪宣泄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容易耽误宝贵的处理和应对时间。
(二)动摇社会信任与共识引发次生灾害
突发流行病并不是简单地如字面所示归属于卫生医疗问题,它实际上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疫情研判、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经济秩序、国际影响等,特别跟政治的联结是非常紧密的。而西方政治文化中通过隐形意识形态手段操纵事实在特殊时期则大有可乘之机,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不实或者“双标”报道。但突发流行病的解决需要社会间的合作与信任,一旦被偏执、欺诈、玩弄、造谣的混杂价值所裹挟,对于尽早度过突发公共卫生灾难形成了阻碍,不仅稀释了民众对主流价值的信任,还容易对社会和个人造成次生伤害,包括网络民粹、恶意攻讦、末日绝望等。
(三)非理性情绪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高压
网络上看似集体无意识的讨论,其实很容易受他人的观点左右。貌似义愤填膺的正义感凌驾于事实和真相之上,现实的紧张感加剧加之集体中个人身份被隐藏,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更加严重,朝着偏见方向前进最终可能形成极端观点,不理性一集中就会酿成严重后果。突发流行病有它的学理规律,特殊时期真相的定论会延迟,而网民一般缺乏耐心等待事件的真相或起因经过的全过程,比如网友评论不假思索地“秒回”显然是缺乏思考的行为。此外特殊时期公众更会带着放大镜看问题,负面与极端给注意力经济更多的流量,夸大负面“爆点”引导社会情绪,容易引发怨恨式评论。而平时能够正向发挥“窥视镜”和监督窗口作用的机制此时不一定畅通,网络监管的“一刀切”就会更加集中,社会现实的呈现和稳定和谐的媒介生态容易失衡,形成恶性循环。还有信息过载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挫败、失落、焦虑感的滋生,偏离和纠偏也在考验着大家的承受能力。
四、结语
全媒体时代人们容易产生极化认知,后真相用视角创造事实,撕裂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等共识价值,如后真相话语滥觞,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很难逆转的。在此趋势下,对于信息传播中的后真相迷局需要采取针对性的破局措施。
廓清后真相需要净化网络环境的国家队,不是依赖于删除或者断网这样的刚性抹杀策略,而要遵从、执行法律,设置底线边界进行管理。我们可以依据国家公信力建立科学辟谣平台,建立舆情信息净化机制,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果断介入阻断,规范信息媒介和平台管理,文明上网,将理性发言与普法教育结合起来。再者,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提升尤为重要,通过主流的不缺位来应对后真相的占位。顺应潮流,利用好信息在设置议程和构建真相方面的作用,整合资源增强正向引导和输出,兼顾家国情怀,增强包容性,不能局限于强化宣教,要在宏观的角度讲理论讲视野,在微观的层面重事实、重关怀,化抽象理论为接地气的观点,善于运用情景交融等新方式,从话语的“传输”走向话语的“传播”,对多元价值进行重构,当然这种重构要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
除了他律,自律也是需要倡导的,媒体应当涵养社会责任与法律意识,加强网络媒体行业的自律建设,不能仅仅追求“10万+”,而需要谨慎、客观、公正的态度,结合舆情的敏感性做好解释披露等新闻报道工作,促进公序良俗的不断完善。对于个人,特别是处于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波动期的青年,应当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升信息素养,形成思想和人格的独立,而不是简单地随波逐流,任由情绪裹挟,形成不良的价值判断。
作者简介:汪卓群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团总支书记、专职辅导员 助教
参考文献:
[1] 徐天博.“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2):135-140.
[2] 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01):115-132.
[3] 龚群.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J].探索与争鸣,2017(9):55-60.
[4] 李平,许高雅.“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研究——以重庆公交坠江案为例[J].新闻前哨,2019(10):51-52.
[5] 宋凯,袁奂青.后真相视角中的网民情绪化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8):146-15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