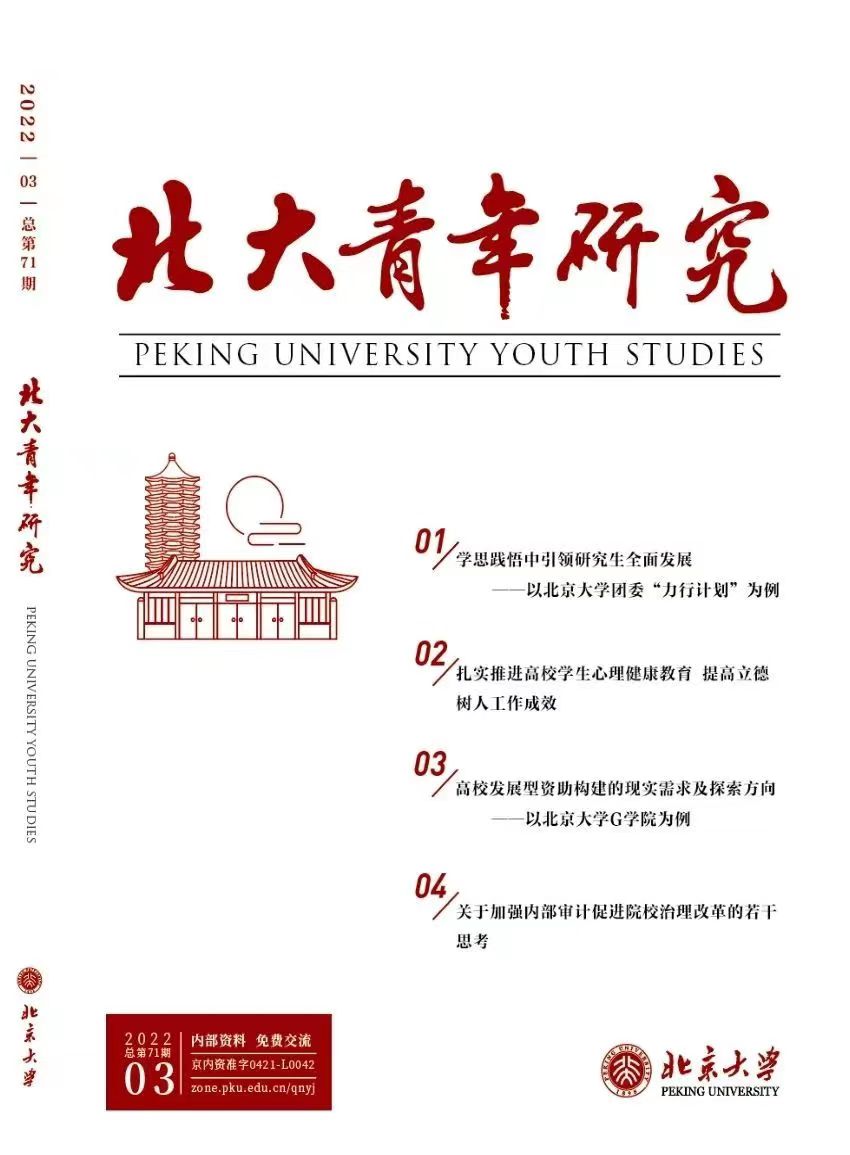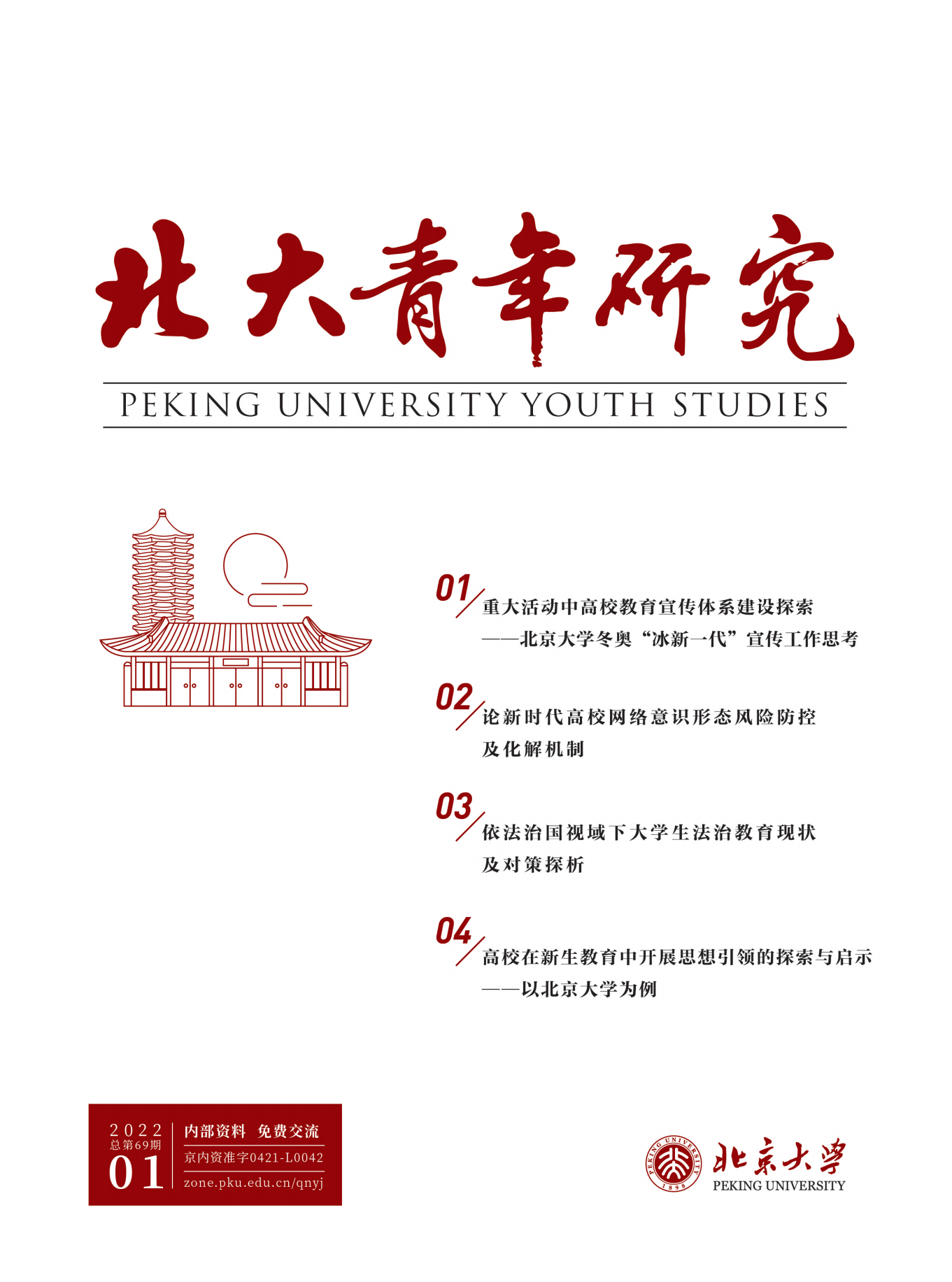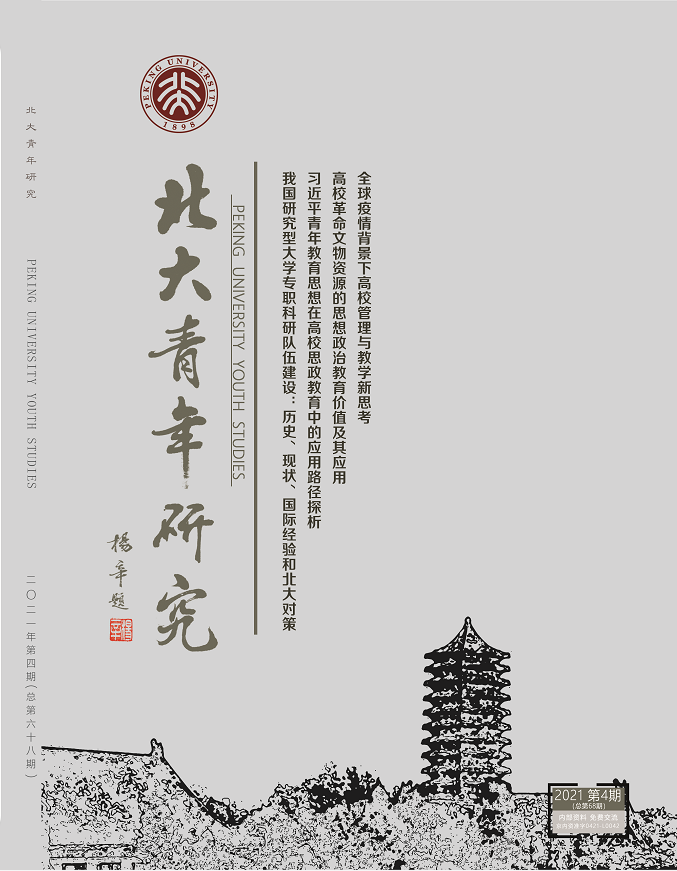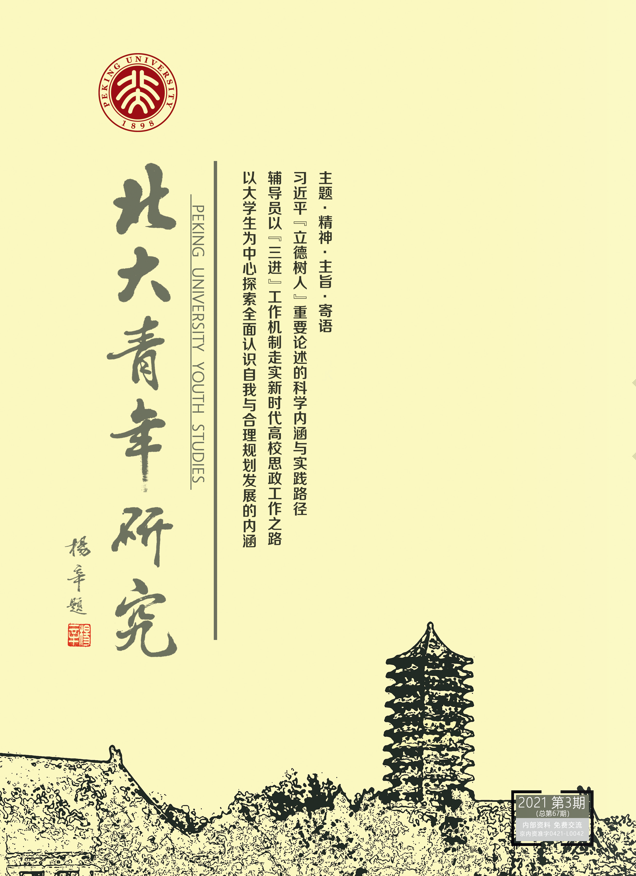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人民”与“民族”双重变奏下的初心与使命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和“民族”作为核心要素,人民性问题的重置和新型民族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一环。在当下进一步深化人民与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步入新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人民;民族;意识形态;初心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前苏联列宁等人的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欧陆与北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坚持相同的思想基调,但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有着诸多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不同之一就是有关政党的理论。习近平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其中有两个要素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中国人民”,其二是“中华民族”。二者共同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的身份确认画下了独特的边界。
一、 “人民”范畴的再意识形态化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首先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人民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纽结,这一范畴中暗含了辩证的否定性。这种辩证的否定性指的是它指认并批判着与“人民”,或者说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社会主体(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又肯定着这些对立的社会主体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人类社会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一旦落后的生产关系被变革,他们依然可以被纳入到“人民”这一范畴中来。
这一范畴在我国的理论建设中经历过一系列意涵上的转变。它曾长期被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性”实则就是特定的“阶级性”。而当外族入侵的时候,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又抹去了“阶级性”,转而强调血缘、地缘上的共同体意识。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实事求是”、“不争论”(保留阶级政治意识,但不鼓励社会舆论对此进行讨论)等方式将“人民性”实际上转化为了一定程度上的“物质性”,即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解放物质生产力,而这又促成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
而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这一概念再一次被凸显出来,此时它与“初心和使命”这两个概念关联在一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的回溯性。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3]。这与毛泽东有关“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一致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强调的“合力说”(即历史展现为众多特殊主体意识交锋后保留下来的共性原则,个别英雄人物无法依靠其特殊性改变此普遍性)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邓小平理论中也强调“群众路线”,但是邓小平意义上的“群众路线”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强调的是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足服务,人民的物质需求才是最本质的需求。换言之,他强调的是“群众路线”中去政治化的一面,即他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的“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4]而在习近平这里,他强调的正是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再政治化的处理。他指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5]这一判断面向的主体是共产党员在思想上要树立群众主体性意识,直接呼应着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这表明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党的政策方针上要在算好经济账的同时算好政治账,以优化政治生态的方式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底色的中国。
在“人民”的概念中重新置入政治性即重新置入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一词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常常呈现贬义的色彩,因为“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的,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7]此处,习近平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同样也是一种创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表述是“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8]。由于人为了生存必须生产,所以他们必须活动于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为了适应此基础,他们的意识就会被适应经济生活的生产活动改造,“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9]“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10]。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是那种让人及其目的分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在此意义上反对信仰信念,因为他们坚持如果人的思想和其本质目的相统一,那么便不需要外在的思想对其进行额外规定。习近平对“人民”的再意识形态化强调的是人民必须成为主体,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必须让人民以人民自身的需求为自身目的,而不在人民之上强加任何额外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正表明,为中国和为人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必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就是人民的意识形态,对党的信仰同时就是对人民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外在的,而是内生的。这正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政党理论上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的人民观又是我党群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将再意识形态化的思路提到议程上来。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这绝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绝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11]“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12]。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党员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自己的“先锋队”身份,提升自己的政治素质,社会不再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导向,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需要政治意识。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将人民性的问题提升到党的初心和使命上,将其指认为党的核心诉求,正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承前启后的姿态迈向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产主义特质
为“中华民族”服务同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理论归纳。习近平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3]这种论断提请我们注意,中华民族的问题和中国人民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只有民族的复兴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简言之,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看,民族问题的最优解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紧密相关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各民族必将走向融合,最终“民族”这一范畴将被“共同体”取代。一些理论据此认为共产主义和民族是水火不容的,他们中的一些论者以波兰在20世纪30年代的境遇为事例,指出当面对外来入侵的时候,民族会阻碍共产主义的实现,因为当民族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该国家内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趋向于联合对外,此时阶级矛盾的解决被民族矛盾的出现无限期地延宕了。而且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正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据此,这些论者以马克思那句著名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来使共产主义和民族问题处于难以调和的关系之中。
然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将“民族”视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民族融合在马恩的语境下指的是民族冲突、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在共产主义实现时不再出现。反对者所指出的诸多反面事例同样也正是马恩所反对的。民族矛盾延缓了阶级革命的进程正说明不平等的民族共同体必须被取代,只有当国际环境和平稳定的时候,社会变革才能按照其既有的规律展开;而民族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一面亦正产生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只有当民族关系平等了,国家在民族压迫上的一面才能被真正取消掉。“民族”这一范畴必然要被扬弃,“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义上来说,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范畴和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必须被取代,他们并不是说要让各民族变成同质化的群体,也并不是反对各民族在独立平等的意义上形成区域自治的共同体,相反马克思就曾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某种优点”[14]“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15]因而有着在世界舞台上不可取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习近平的民族观实际上沿承追溯的正是马恩意义上的民族理论,只不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讲民族,而习近平则是从民族的意义上来讲共产主义。民族的独立、民族的富强是摆脱和避免被其他民族剥削和压迫,避免与其他民族产生不必要的冲突的基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多民族均被视为世界历史的平等主体的理想。这也就意味着在国际视野下,我们必须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来看待民族问题,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不同于资本主义以资源攫取和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斗争性、掠夺性的资产阶级世界秩序。它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16]
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表明,世界舞台上共同体的出现是一种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必然。这一共同体最初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确立下来的,马克思判断“随着工业生产以及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割和对立日渐消失”[17],正是由于资本主义那种将原料生产和原料加工分别置于不同国家之中的生产方式,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体才第一次出现。但是这种共同体最初是不平等的,在这一共同体中,殖民地民族始终受宗主民族的压迫。以此为出发点,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单个民族的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共同体内各民族主体平等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共产主义革命依据各民族的特征可以有不同样式的呈现方式,一些民族有条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18],从现代化之初就以建设平等共赢的共同体为目标。
三、中国特色与“卡夫丁峡谷”
我国一直致力于以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所谓“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那里的本义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迈向共产主义时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阵痛。而对之进行的跨越则指的是越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以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苏俄对这一峡谷的跨越失败了,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上,发展出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一方面指的是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经济建设的根本受益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是指,我国始终在国际关系上坚持避免资产阶级那种以剥削为底色的共同体的出现,关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周恩来就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鲜明地体现着共产主义所坚持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这些理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发展。它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关系上的平等拓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的平等共赢。这实际上是一次对共产主义进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完善。同时,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特殊国情也为这一民族理论赋予了独特的内涵。习近平指出,“多民族是我国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可以说,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9]
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要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符合共产主义发展要求的有利环境,还是要在中国国内实现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共进。前苏联与当代中国的处境有着一定意义上的相似性,但是前苏联并未能够成功地在民族问题上跨越马克思所谓的“卡夫丁峡谷”,众多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均为民族国家,它们最终未能形成一个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共同体。我国的民族虽然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呈现为一种混合聚居的形态,但是依然有相当多的境外势力试图在中国国内制造“卡夫丁峡谷”,试图强调我国境内的民族可以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这一谬论的根基正是民族间必然存在相互压迫,必然无法实现平等共赢的学说。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内部的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以同行者的姿态一起走向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平等地位,正是这一问题能够解决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在此意义上对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有着先导性的示范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的根本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初心和使命正是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实践目的是不可分割的,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点正在于人民性问题的重置和新型民族观的提出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当下进一步深化人民与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建设,更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步入新阶段的先声号角。
作者简介:安晶丹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团委书记 讲师
参考文献:
[1]十九大学习笔记[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35.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4.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43.
[7](英)汤姆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8][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50.
[10][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327.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7.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1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9.
[16]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3-4-8.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30.
[1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