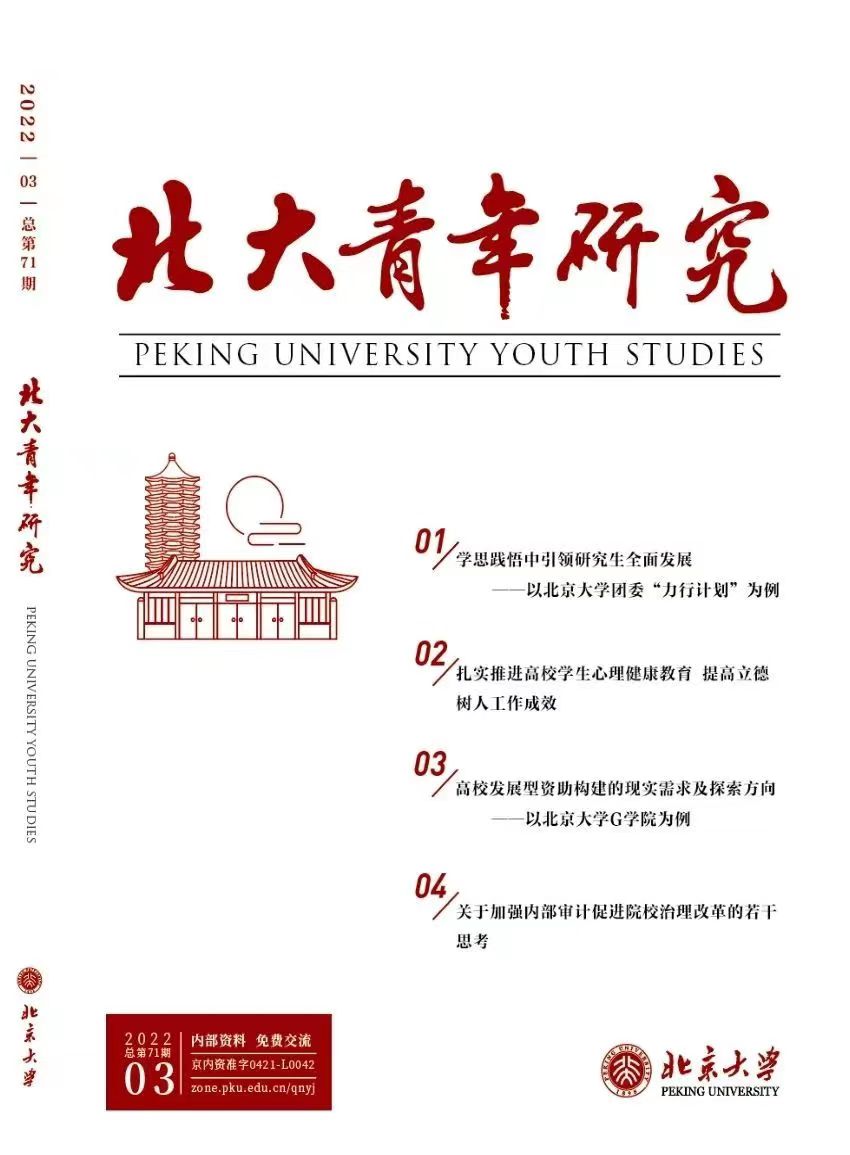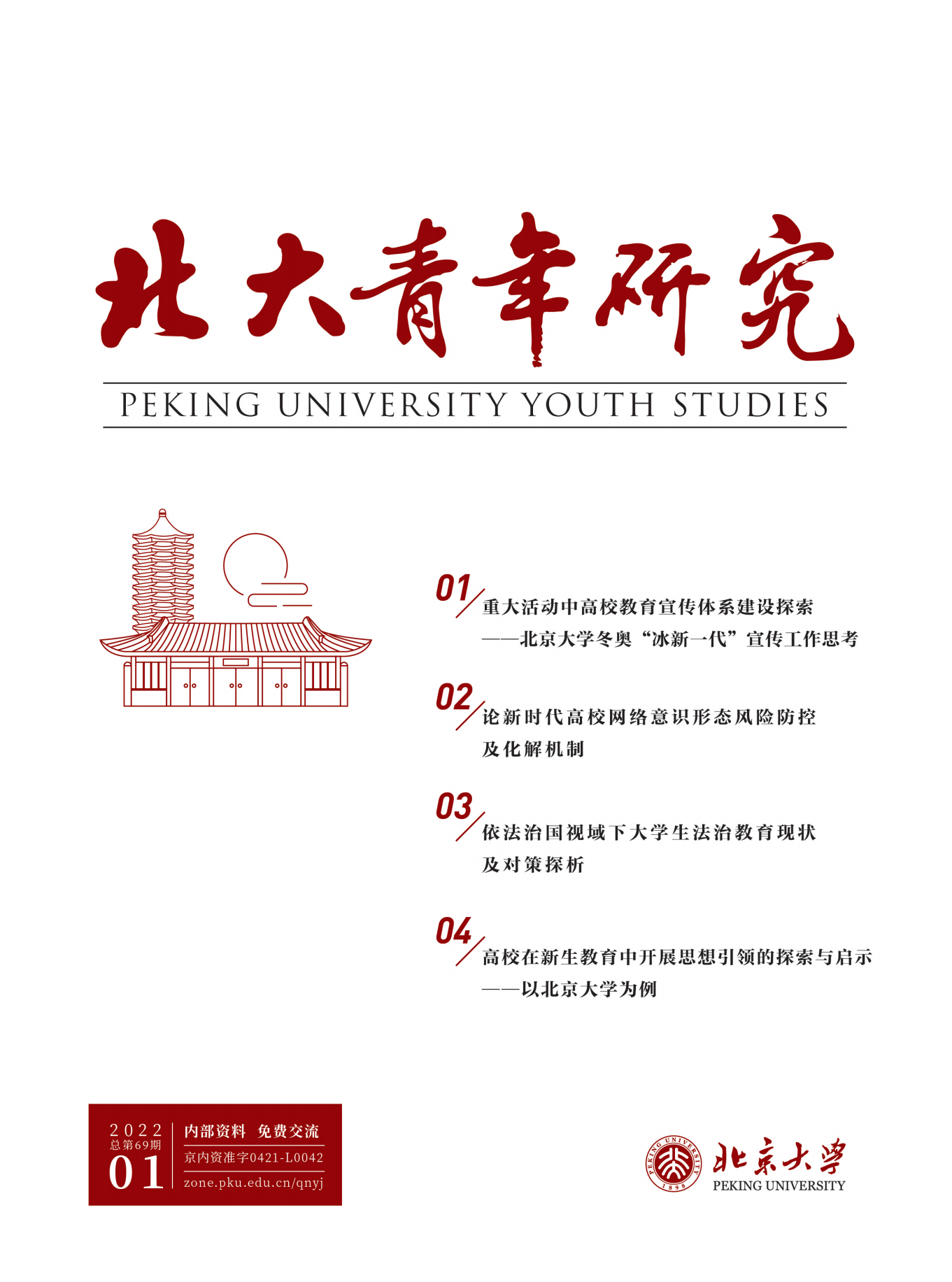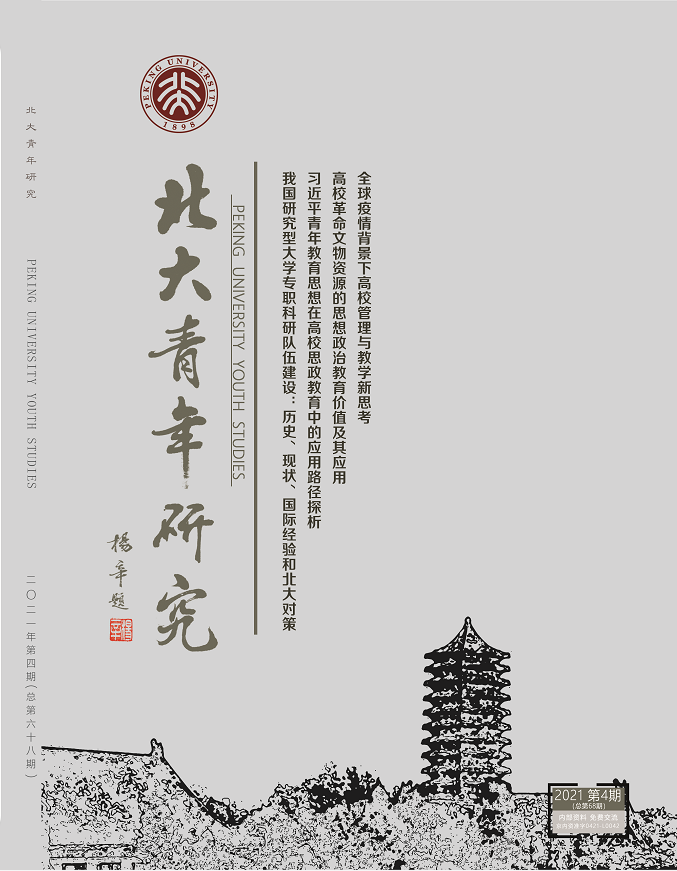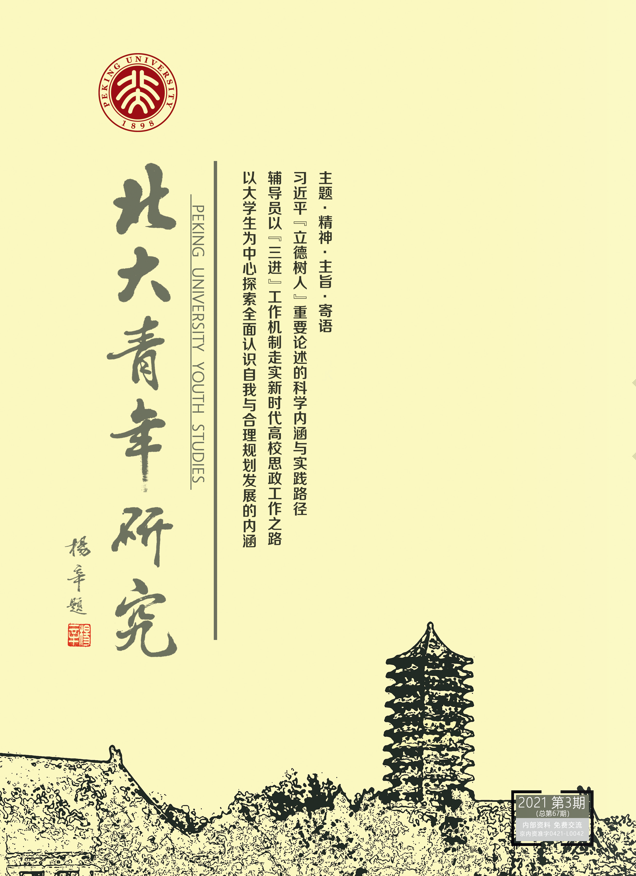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蔡校长的重大担当与卓越贡献 ——纪念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一百周年(一)
今年是蔡元培校长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任职一百周年。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到1926年7月8日正式辞去这一职务,共计十年半的时间,但他实际在校办事只有五年半。时间虽不算长,但蔡元培决不是一般的大学校长,他是一位极具理想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积极吸取西方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立下了“教育救国”,培育杰出人才,振兴中华民族的宏大志愿。因此他能破除疑惑,力排众议,以同盟会元老和前教育总长的身份毅然出长就职饱受争议的北京大学。
那么,身在北大的蔡元培,究竟主要做了哪些事情,有过哪些重大贡献呢?
第一,反复阐明和特别强调大学研究学问的基本性质。为了把受前京师大学堂熏染而弥漫着官僚腐败气息的旧北大,改造成洋溢着科学、民主气息的现代新型大学,蔡元培一来到北大,便反复阐明现代大学的基本性质。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他便鲜明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①]接着在2月5日与天津《大公报》记者之谈话中指出:“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务使学生了解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②]1918年9月20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校长在演说中又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③]在191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他再次重申:“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④]我国近代的书院制,固然有研究学问之性质,但蔡先生的这种定性,显然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学制,特别是来源于德国教育家洪堡所创建的柏林大学和洪堡经验。这就为我国现代新型大学的建设奠定了立脚点。
第二,明确提出和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方针。在1918年11月10日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先生指出大学既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又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就整个世界来说,正如《礼记•中庸》里所形容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各国大学来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⑤]随后,他又总结了我国三千年来政治制度和近百年来教育制度中的经验教训:“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鹜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界断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⑥]于是,在1919年回答林琴南的攻击与责难中,他阐明了对待学术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大字,说明中西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应当相互融合,自由与包含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这个方针的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既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又适应人才成长的要求。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多年教育实践证明,它为教育领域的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它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这是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梁漱溟所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⑧]
第三,提出“健全人格”的培养宗旨。这就是“德、智、体、美”四育结合,全面发展。1920年他在南洋的一次演说中全面阐述了这个宗旨。先说体育,他引用西方的一句格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可见决不可轻视体育。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便会失却体育的价值。次讲智育,他形象地指出,教书“并不是要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⑨]至于德育,并不只是按预定的格言去做。道德是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比如有人讲爱家,有人将爱群,其实共同的原理是爱人。最后美育,是蔡先生特别强调和补充的。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点。他认为美感是共同的,不分你我,人人都可分享,没有利害冲突。审美的趣味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冲淡人的占有的冲动,并促进智育和科学思维的发达,促进人的创造的冲动。美育中的艺术形式多样,各人的个性、爱好不同。有的好书画,有的好雕刻,蔡先生认为,可各随所好,只要能引起审美的兴趣。
蔡先生在校内外作了一系列关于美学和美育的演讲。他在北大唯独开设的课程是1921年9月开设的美学。与此相配合,还在学生中建立了一系列艺术方面的社团组织,如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雕塑研究会,等等,使美育活动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可见美育确实是他的“健全人格”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与贡献。
第四,认真吸取和大力积聚优质人才。蔡元培深知,民族的强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杰出的人才。这种人才只有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所以他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在蔡元培看来,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而要培养出这种杰出人才,首先必须解决学校的师资问题。他认为大学的教师应当是“积学”而“热心”的。就是说,应当在学问上有深厚的积累而又热诚于教育事业。为此,蔡校长在1919年的开学典礼上特别提到:“……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⑩]可见他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建立制度,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的时间,确立对教师的聘任和辞退的规定,对于那些确实条件欠缺或不负责任的教师,他是坚决辞退的(包括某些外籍教师),虽遇棘手刁难,也毫不动摇。同时,蔡先生选择和任用人才,决不偏重资历、学历、文凭,而是注重实际的学识、水平和素养。
蔡先生刚到北大不久,便“三顾茅庐”式地走访陈独秀,并呈报教育部,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长)。1917年8月,他又把年方26岁的胡适请到北大任文科教授。那时胡适在美国还没有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凑巧蔡、陈、胡三人依次年长12岁,都属兔。人们戏称为北大的“三只玉兔”,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三人不单是北大改革初期的主要支柱,北大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所以成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阵地,都与此密切相关。
在文科方面,蔡先生还聘任了梁漱溟、周作人、鲁迅、钱玄同、章士钊、沈君默、马幼漁、刘半农、王建祖、陶孟和、朱家骅、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梁漱溟本无大学学历,而是自学成才。只因蔡先生在《东方杂志》上看到梁的文章《究元决疑论》,从中发现他的佛学水平与见识,便决定请他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先生除了大量选用新派学者以外,也仍然任用了一批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意见或保守立场的学者,如黄侃、辜鸿铭、刘师培等人。针对用人方面的责难,蔡先生回答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11]
在理科方面,蔡校长在头两年里便聘任了王星拱、李四光、丁文江、葛利普(美国古生物大家,1870—1946)、夏元瑮、温宗禹、秦汾、张大椿等人。
第五,加强文理二科,并注重沟通文理,避免学生“专己守残”之陋习,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蔡先生注重“学”与“术”的区分,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门实用学科,如工商、法律、医学等,都是“术”,而纯粹的非实用的科学或哲学,则是“学”。学重原理,术重应用。他说“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理;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么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12]这正是他重视哲学,加强文、理两科基本理论建设的根据所在。蔡先生的这种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过分追求功利,太重实用性了,因而忽视基本理论的倾向比较严重,这是值得反思和警惕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长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否与此相关呢?
在着重设置文科与理科的同时,蔡先生又注重防止学科之间的隔离,防止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他指出学生中的某些偏狭观念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13]因此,他要求《北京大学月刊》发表各方面的学说,提供学生阅读。在课程设置和选修规定上,要求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某种课程,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课程,使文科与理科学生得以互相沟通和互相补充。这正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要求,也正是国际上通识教育潮流的要求。
第六,厉行学制改革。吸取西方国家先进经验,他极力主张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又称单位制,亦即当前所称学分制。这项改革首先在北大实行。学生学满若干单位(学分)即可毕业,不必拘定年限。意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个性。
第七,建立“教授治校”的原则,防止以往由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包办校务的弊端。蔡校长决定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第二部组织各门教授会,然后再组织行政会议,建立一套民主管理的治校制度。评议会为学校最高立法与权力机构,由校长、各科学长和各科教授选举评议员组成。评议会在1917年秋便已组建,12月又由评议会通过了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在蔡校长主持下,按学门分别成立了教授会。这样雷厉风行地健全制度,完善组织,便切实保证了“教授治校”原则的实现。这样,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第八,积极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北大和国内讲学。比如1919年聘请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两年多;1920年聘请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近两年;1922年聘请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来北大讲学;等等。这些讲学在国内教育和学术界有着重大而长期的影响。此外,还曾聘请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波兰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来华讲学,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第九,实行学生自治。首先是在学习上,同时在生活上,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生活上主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这样,在走向社会时,也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第十,1920年2月,第一次招收女生,在全国开创男女同校的新风。
可能有人会问,蔡先生不在校内的约六年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可以说,除了极短的因病治疗和休养时间外,他都在日夜操劳地为北大的改革与建设,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奔波。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到欧美各国进行考察、访问、交流,吸取经验,或亲自联系、交涉、处理各种与教育相关的问题。
1920年10月20日,北大学生为蔡校长出国考察开会话别,蔡先生谈到他“出去的意思有好几层”。大致是:1.了解战后各国将少数人所上的大学,改革为普及性、平民性大学的状况。2.了解、考察在国外学习、用功研究的留学生,并请各大学里的大学问家负责介绍,预约深造,以便将来校内人才的聘请。3.亲自去采办校内所需的仪器设备,采集某些国内所需的艺术真本或摹本。4.校内图书馆当时的设备与藏书都很不完善,由于经费不够,当时的北洋政府不予供给,只好向国内外各方面尽力募捐。5.亲自一再与西方各国政府商量,将能够收回的庚子赔款用于扩充国内高等教育和培植留学人才。
实际上,蔡先生在校外、国外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从《蔡元培年谱长编》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蔡先生无论在校外、国外,他每到一座城市,每走访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多半都要应邀发表演说。蔡先生与胡适先生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也是演说家。蔡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的演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涉及教育、文化、哲学、美学、伦理、历史的方方面面,因而极受欢迎。他既勇于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与经验,又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和他本人融合中西的认识与见解传播出去。他在中西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上所做的工作与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还应看到,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是北洋政府统治,正是军阀混战、各种势力纷争,社会极不安宁的年代。学校经费奇缺,常常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基本的物质条件与正常生活缺乏保障,教员辞职、学生罢课的事时有发生。在这种艰难环境下,蔡元培不畏强暴与挫折,坚持教育救国的主张,在北大厉行改革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开一代先风,是何等的不易!卓越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回顾当年蔡元培的处境与担当时,深切感叹地说道:“……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阀,安福贼徒,袁氏余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14]
纪念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一百周年,学习他的崇高品格与宽阔胸怀,努力继承和弘扬北大的基本传统,培养健全的人格,认真求学、治学,百折不挠地立志成才,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这就是我写本文所对青年同学的期望。
作者简介:张翼星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7.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A].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1].蔡元培.答林琴南函[A].北京大学日刊,1919-321.
[1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3].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A].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14].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A].转引自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