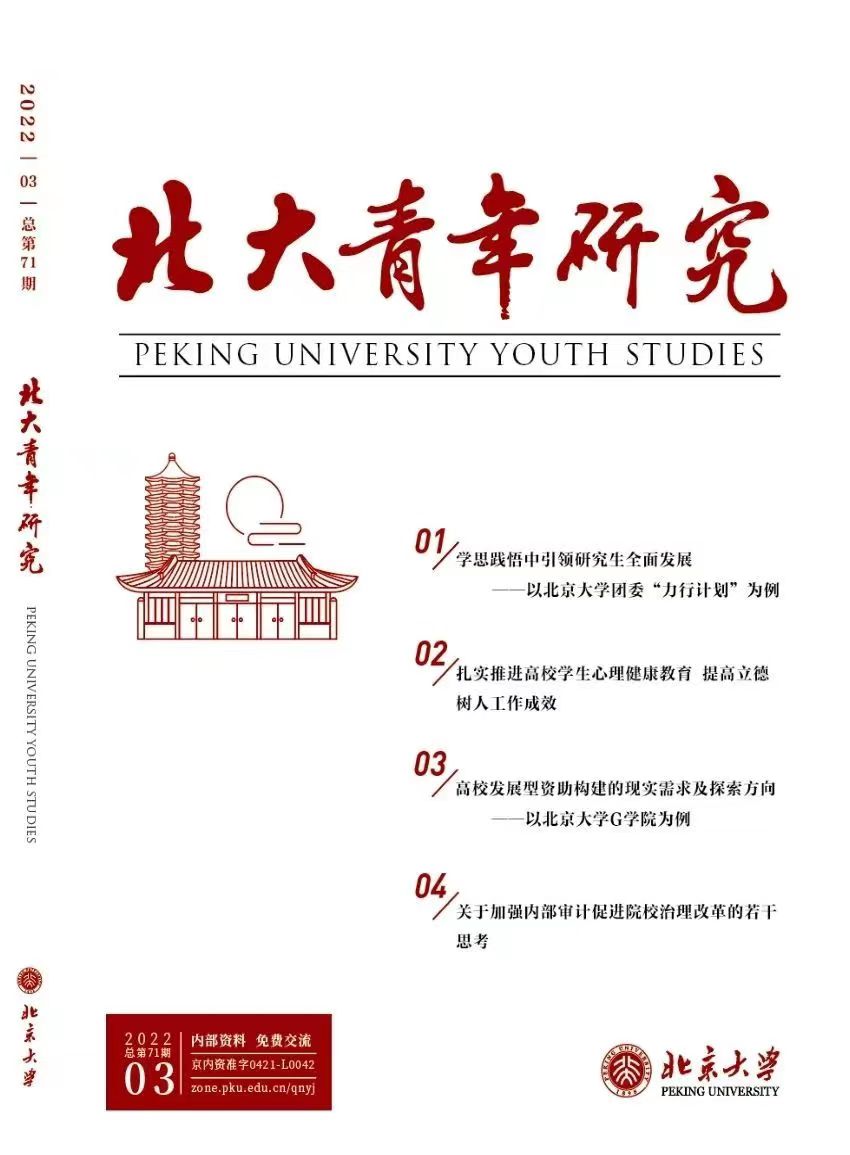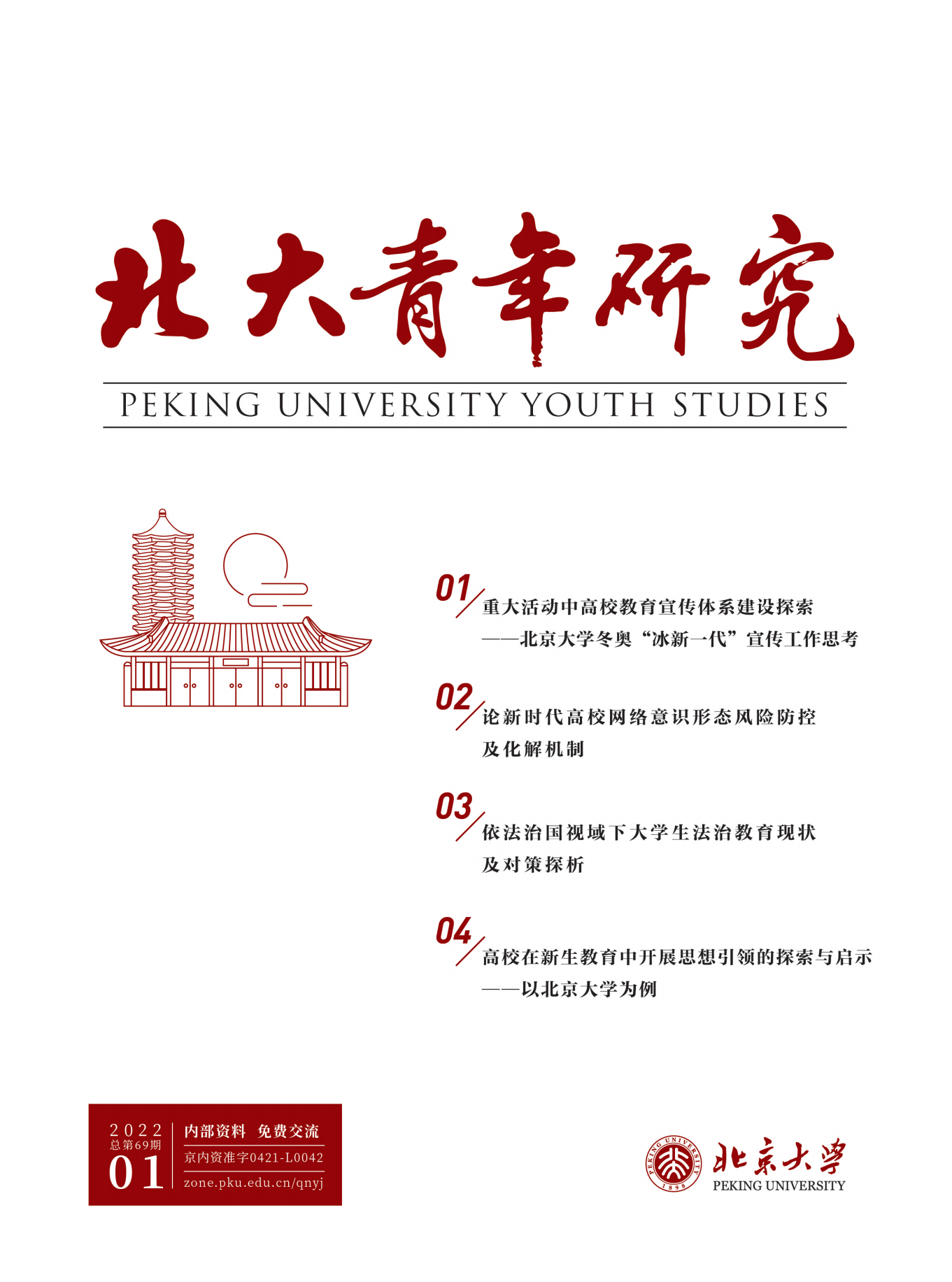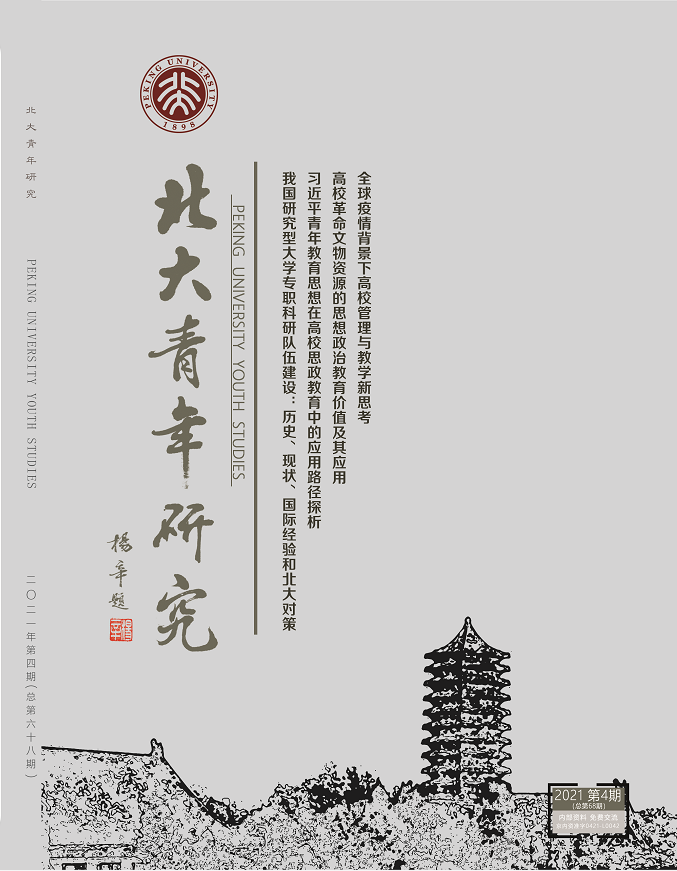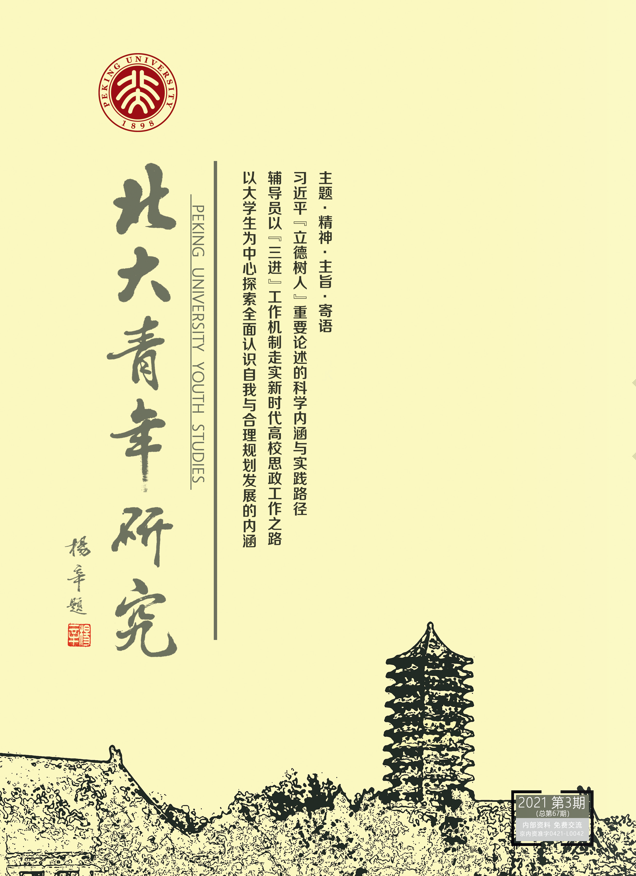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思变: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对“慕课”浪潮的反思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网络时代遇到的挑战大于机遇。慕课是思政课供给侧改革的一次试水。从思政课本身的属性来看,两者的兼容性并不是最好的,要理性看待思政课的慕课化改革。慕课对于改善思政课教学起到了一定作用,传统课堂和慕课可以实现包容性发展。
关键词:思政课;慕课;网络
互联网已经全面而深入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也不例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思政课的改革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慕课”(MOOCs,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等网络课程的引入,是思政课在网络时代“思变”的集中体现。思政课在网络时代面临怎样的处境?“慕课化”改革是否具有普适价值?这都需要结合思政课自身性质与特点,进行冷静而深入的思考。
一、思政课“遭遇”网络新时代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曾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借用这段话来形容网络时代思政课的处境,也是很恰当的。“这是最好的时代”,网络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应用,不但能让思政课教学变得内容丰富,形式炫酷,而且还能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利用网络空间,使思政课无所不在。“这是最坏的时代”,由于信息渠道的多元与便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占有者和垄断者,师生之间知识壁垒几乎被熨平,相反学生对新知识的更新速度甚至更快一些。半部论语治天下,或仅凭一本武功秘籍或口诀就能成为一代宗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师道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对于思政课教育者而言,权威被解构,话语权被分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网络时代,仿佛人人皆可为尧舜,大V林立,公知辈出,一个商界、文娱界、体育界的明星摇身一变,就可能凭借网络成为国民导师,站在人生智慧的至高点上,为你指点迷津。“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因为不仅有可能“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现在连哲学都是了!很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网络推送的。标题党和浅阅读的时代,使得人们失去了深入思考、明辨是非的习惯甚至能力,许多叛经离道、甚至荒诞不经的观点或“学说”因为抓住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广泛传播,网络欺骗和误导成为一种“朋友圈新常态”。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某些公知大V的一些鸡汤文或反主流檄文仅凭标题就被众粉丝怒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深以为然的信仰,不假思索的虔诚。“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多元的价值输送渠道导致信仰的迷茫,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迷失,官方渠道和思政课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育,经常被武断地无视或怀疑。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思政课在网络时代遇到的挑战大于机遇。尤其是传统课堂讲授的效果,网络时代不如前网络时代,这不是一种武断的逻辑推演,多年身处教学一线的思政课教师大都有类似体验和发言权。网络和社会自媒体削弱先赋社会资源和地位对意识表达和传播的影响,突出了权利平等、蔑视权威的观念,而且网络平台便于细分群体,强化认同,密切交流,为亚文化和多元价值的酝酿和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观念和土壤的形成,“对教育者的权威角色和垄断地位产生了剧烈冲击,稀释了单向度灌输的内容;网络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则通过对一般风气的侵蚀,对教育内容和效果产生了逆转和阻碍。”
二、思政课与“慕课”的兼容性思考
国内有些高校,尤其知名高校将慕课进入思政课,是思政课迎接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变法图强的一次尝试。但国内外对慕课本身的评价,尚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慕课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在未来十年为高等教育的组织和运行带来根本变化,是一种“颠覆性的革新”,是一种民主力量。反对者对在线课程的扩张感到恐惧,担心教授们的饭碗将被电脑夺去。在反对者看来,慕课是被过分吹捧起来的泡沫,是对教育核心价值的破坏,是高等教育被无耻政客劫持并与商业机会主义沆瀣一气的最糟糕结果,是造成社会不公正和经济剥削的工具。反对者的理由虽不无道理,但也容易招致本位主义和“小家子气”这样的诟病,而且慕课本来就是以打破教育资源的壁垒,推进教育公平的名义而进行的。如果说慕课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主要是学习体验(而不是娱乐体验)和完成率(学完而不是刷完)的问题。我国学者在研究了国外诸多慕课案例之后提出,“从前是狂热战胜了现实。人们曾对慕课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待它是一场‘让天下所有人免费上课’的革命。但当人们发现慕课的结业率只有5%,对学生的要求又很高,教学方法也没有多少新奇之处等问题之后,失望情绪自然难免。”慕课热之后的冷思考,不是完全否定或扼杀慕课这一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而是理性思考慕课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慕课等网络课程是否适合所有类型的课程,什么样的课程更适合引入慕课,而什么样的课程不太适合。慕课等网络课程能否成为改善或拯救思政课的“一针灵”?这需要结合思政课本身的性质与教学特点进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区分“我要学”和“要我学”的课程。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我要学”的课程,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慕课等网络课堂形式,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且慕课由于其时空的灵活性和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在这些课程领域会大有作为,也会广泛“圈粉”。另外一类课程是“要我学”的课程,思政课应该属于这一类型。思政课承载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而意识形态教育,往往不是受教育者自发的需求,而是教育者主动施予的过程。正像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慕课等网络教育由于缺乏理想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在这类课程上可能会遭遇诚信危机。倘若老师声嘶力竭、汗流浃背的面授课都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关注的话,如何能够奢望学生们在私下会夜以继日地学习课程视频?!
其次,要区分“知识性”和“体验性”课程。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将“教书”和“育人”分开讲,前者指专业知识的传授,后者则是修养修身的过程。前者和职业有关,后者和做人有关,和思政课有关。专业类课程,基于安身立命的功利主义,往往会变成“我要学”的课程。育人类课程,尽管从“先做人后做事”的人生哲理来说更为重要,但是基于其效果的隐性和滞后性,往往会变成“要我学”的课程。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从教育重点和教育规律来看,专业类课程可能更注重“知识性”,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慕课等网络课题,都可以承载。育人类课程则更注重“体验性”,即注重思考和修养的过程。上课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体育课就是极端的例子,体验性比知识性更重要,网络永远都无法取代操场和跑道。(但也不否认,计步器等网络软件的普及,方便了监督计量,甚至激发了人们健身的兴趣,这是网络发展值得称道之处。)思政课也是注重过程体验的课程,假如可以把理论修养课,比作西天取经,真正让猴子成佛的,不是最后取得的经书,而是取经的过程,否则猴子一个跟头翻到西天,经书是立等可取的事情。经书这个期终成绩只是他最后取得的学位证书,而作为学历证明的毕业证,则体现在“九九八十一难”的过程中。思政课堂的参与者可能对参与过的活动和自己准备过的课题,印象深刻,对于某个老师的某些方面的特点、魅力或金句,印象深刻,而对于具体讲了哪些成套的理论或知识体系,印象可能并不深刻了。这充分说明了思政课体验性和参与性,大于知识熟悉的特点。慕课等网络课程设计的初衷,就是适应大学生使用网络的习惯,旨在增强学生体验性与参与,但是如果过程监督和考评不利,就会事与愿违,甚至连传统课堂的体验都不如了。网络可能方便了教学,但是教学本身可能也需要面对面地进行实践,而不是一味的迁就和迎合。
最后,要区分“喜欢选这个课”和“喜欢上这个课”的本质不同。喜欢选这个课和喜欢上这个课是不同的概念,假设思政课上课放羊,考试放水,那么这种课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慕课,由于学分好混,都有可能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但他们喜欢选这个课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上这个课。官方倡导的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肯定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还得以使学生“终身受益”作为根本目标,尽管这样目标尚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但任课教师不能从一开始就放弃努力。即使获得学生的好评,也要理性甄别,课程是满足了娱乐体验,还是丰富了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否则就背离了思政课的初衷。
慕课使得思政课程被商品化是商业资本介入不可避免的属性,但是如果思政课程被娱乐化了,则是官方和教育者都很难接受的结果了。区分“喜欢选这个课”和“喜欢上这个课”,就是要提醒教育者和决策者不要被表面的点赞所蒙蔽。尽管这种区分没有直接针对思政课传统课堂和慕课的优劣,我也没有对哪种课堂更受学生欢迎做过大样本研究,但是这种思考提醒后来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要综合并深入思考学生民调中“喜欢”或“支持”这个选项。在北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上,300人的问卷中有2/3更支持传统课堂,但这种多与少的支持率,可能和学生对慕课缺乏必要的了解有关,就像全国绝大多思政课是传统课堂,只有个别学校选择了慕课,这也并不说明传统课堂更受欢迎,因为慕课是新生事物,它的时段才刚刚开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思政课与专业类课程相比,与慕课的兼容性并不是最好的。但为什么思政课慕课改革的热情,甚至高于其他知识类课程呢?(对比数学课可能还在板书时代)举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为什么治疗感冒的方案和药物多年不变,而治疗癌症的新药和方案却层出不穷呢?(尽管这些努力没有一个具有突破性进展。)这个比喻不是想说思政课业已无药可救,而是想突出它的性命攸关的地位。对于它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尽管尚不存在“一针灵”的方案,但是也不能放弃治疗。慕课和网络课堂的改革,是一种思变的尝试,尽管其兼容性和实效性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但如果理性地看待和发展慕课,其仍然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三、传统课堂与“慕课”的包容性发展
技术不能取代课堂,但技术必然会改变课堂。就像PPT技术普遍(但不是全部)代替了板书而改善了课堂效果一样。网络时代的特征和慕课的一些优势,值得思政课传统课堂反思和借鉴。而思政课传统课堂坚守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属性,也为慕课的优化与兼容性改造提供了遵循,两者可以实现包容性发展。
传统课堂是思政课教学的主阵地。如前文所述,网络时代的价值多元和与网络亚文化的冲击,已经使得这块阵地“易攻难守”,但这并不是广大思政课教师放弃阵地或转移阵地的理由。主阵地不能放弃,是因为大学生思政课承载着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使命,“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主阵地也不能转移,至少目前尚不具备将思政课堂全部转移到慕课或网络上的成熟条件。相反,广大思政课教师应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程的理论高度和课堂品质,重新赢得学生,赢得阵地,与时俱进显得比以往更为迫切和重要。网络时代的思政教育更主张学生的主体作用,理论上也有单主体说和双主体说等纷争。但笔者认为,教的过程,教师永远是主体,学的过程,学生永远是主体,这在任何理论框架下都是成立的,只不过在教与学的设计比例上,以及在对教育效果的贡献上,不同的观点会区分不同的主次而已。教师始终是不能放弃教学的,尤其是面对面教学,否则大学生和自学考试的学生有何区别?慕课中的大咖秀,一方面给传统课堂带来了竞争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借鉴。另外,慕课以学为本的价值取向,也为以教为本的传统课堂,在加强学生参与方面提供了启发。
以北京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课堂教学与学生参与各占一半的比例,后者甚至更多一些。专题教学要做到少而专,专而精,每讲一个专题,都会布置相关阅读书目和课题研究,课堂分成若干小组,相关小组的学生,每人要完成相关主题的读书笔记(若干),同时还要分组集体完成一个主题的课件演示,在接下来一周的讨论大课堂上,几个课题小组进行课件主题演讲PK,接受广大同学的评论与挑战,老师进行点评,尽管这也类似慕课翻转课堂的形式,但是师生的讲授和讨论,都是在课堂上面对面完成的,学生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也是在线下完成的。
慕课引入思政课,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不同的学校,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慕课天生就具有大咖秀的基因。因为从它诞生的源起,以及商业运作的机制来看,都是明星学校、明星老师、明星课程的在线推广,从商业的角度说,这样的课程才有卖点,换成教育的语言,就是整合推广优势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公平化。我国思政课的慕课改革,是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率先开始的,因为这些学校就是优势教育资源的代名词,这既反映了正确的商业眼光,更体现了强者的担当。他们是思政课供给侧改革的先行者,也是慕课商品化比较“适格”的供给者。而其他绝大部分大学,都可能作为潜在的“买家”而存在。笔者不否认名牌大学也有相当平庸的老师和课程,也不否认普通大学有相当明星的老师和课程。但是教育资源的优劣比较还是存在区别的,因此不处于优势地位的学校和课程,不宜基于随波逐浪的热情而投入慕课的研发中,因为这种重复建设和过度建设,容易形成资源浪费,而且市场前景堪忧。如果说仅仅是基于本校教学自给自足的需要,将自己的课程翻转成网络的形式,过一把“小咖秀”的瘾,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不符合慕课本身大型在线开放的定义和形式了。其实目前上述名校的慕课,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慕课形式了,而是针对思政课的特点,进行了兼容性改造。真正的慕课是自由选课的,而思政课作为学生必修课,是必须选择,必须完成的。真正的慕课是大型和开放到难以组织统一的线下活动的程度的,而思政课的属性,理应加入大量线下的互动教学。现在各高校思政课引入的慕课形式,更准确来讲,应该是SPOCS(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的形式。本土式叫法是混合式教学法,仍以清华大学为例,2015年春季学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两门课程在组织形式上均是线上慕课学时替代线下学时。其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组织了3次线下讨论,每次4个班,约有100人次参与了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组织了7次线下讨论,每次4个班。两门课程均组织了3次线下专题辅导。这种教学模式,其实是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融合的结果。
对于名校而言,最优势且不可复制的资源,与其说是拥有优秀的师资,不如说是拥有优秀的学生,尤其在这个强调以学为本的时代。对于这样的学生群体,无论是传统课堂,还是慕课,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名校的思政课改革,无论是传统课堂的改革还是慕课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但未必具有普适价值。不同的学校,还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来选择和思考本校思政课线上或线下的综合改革。
作者简介:张会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① 蒋广学等:《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探索实践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② 吴万伟:“‘慕课热’的冷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第1期,第12页。
③ 吴万伟:“‘慕课热’的冷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第1期,第11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⑤ 参见汪潇潇、聂风华、吴瑕:“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的建设与实践”[J],《现代教育技术》,2015年第111期,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