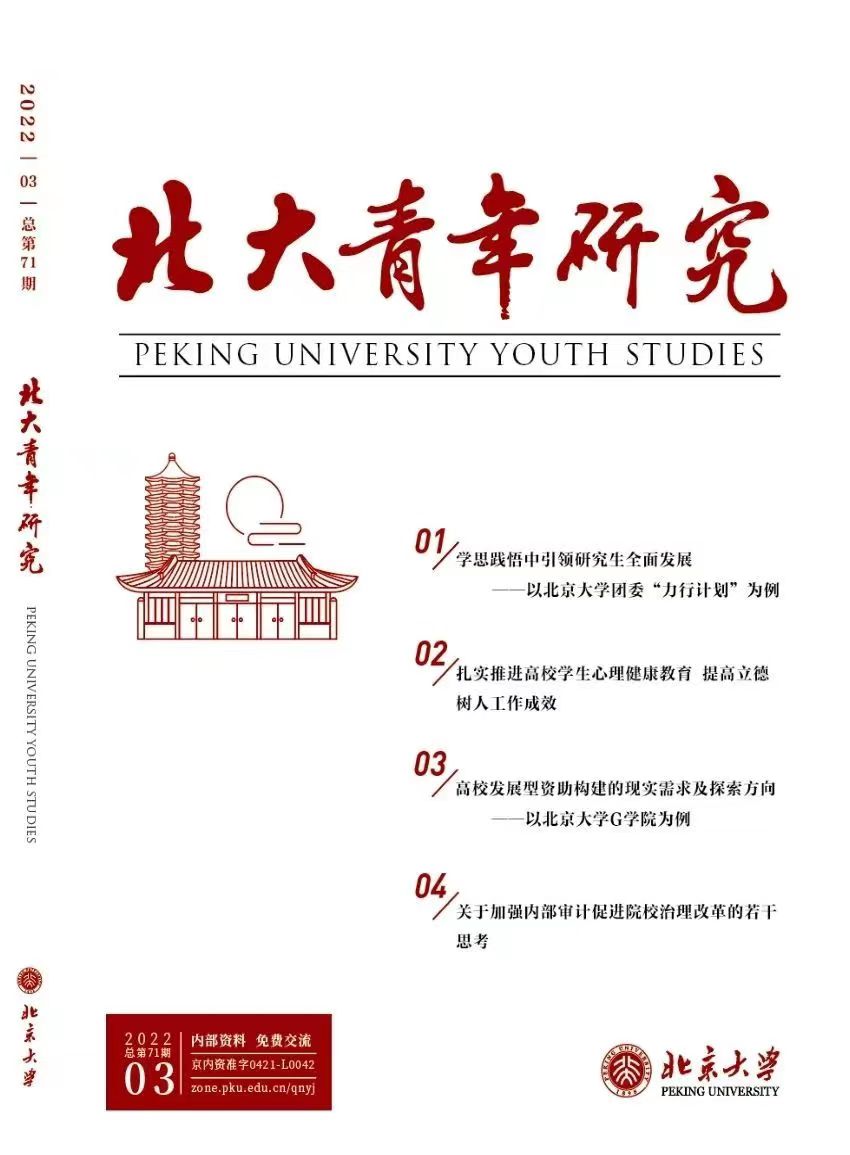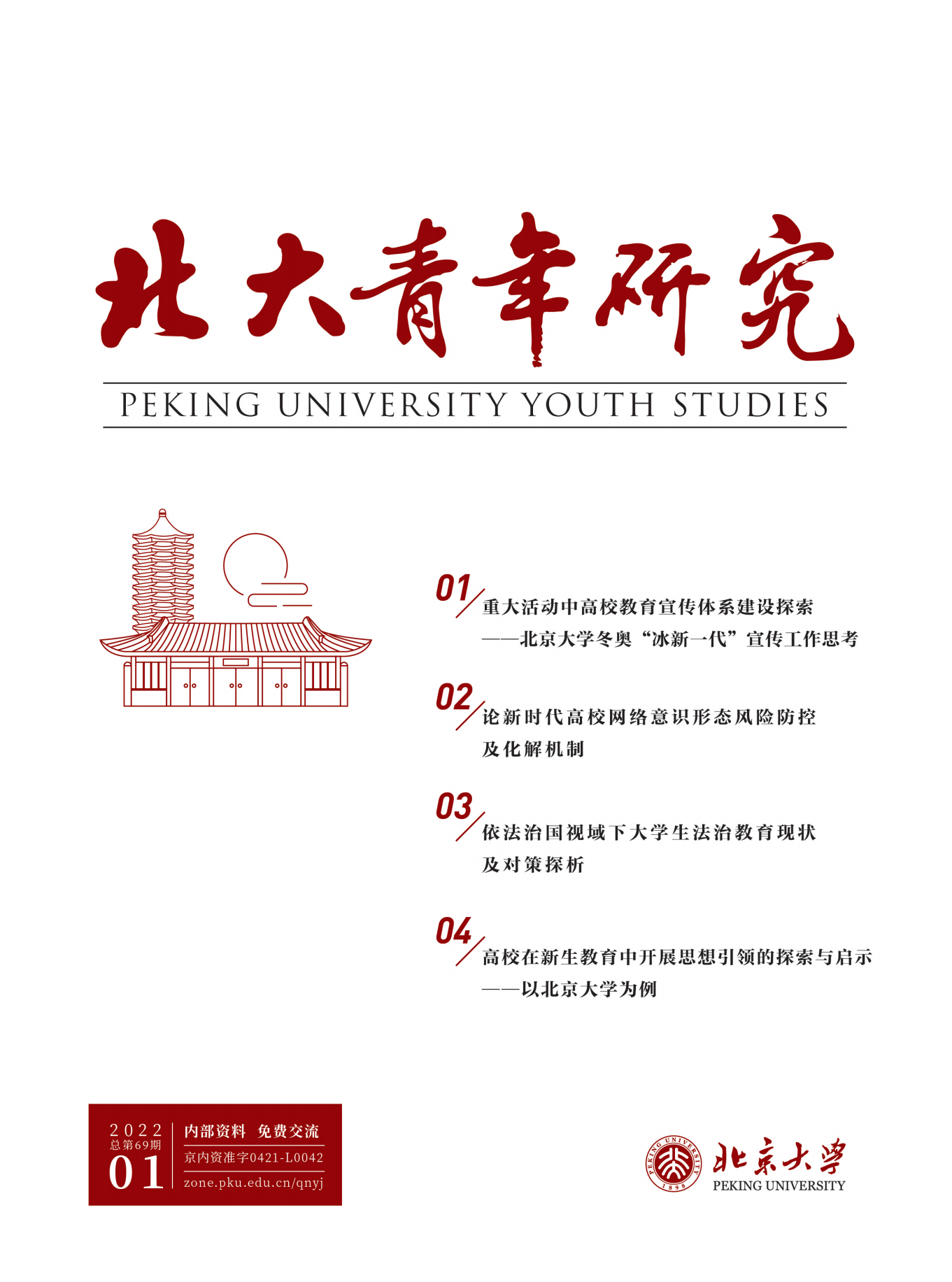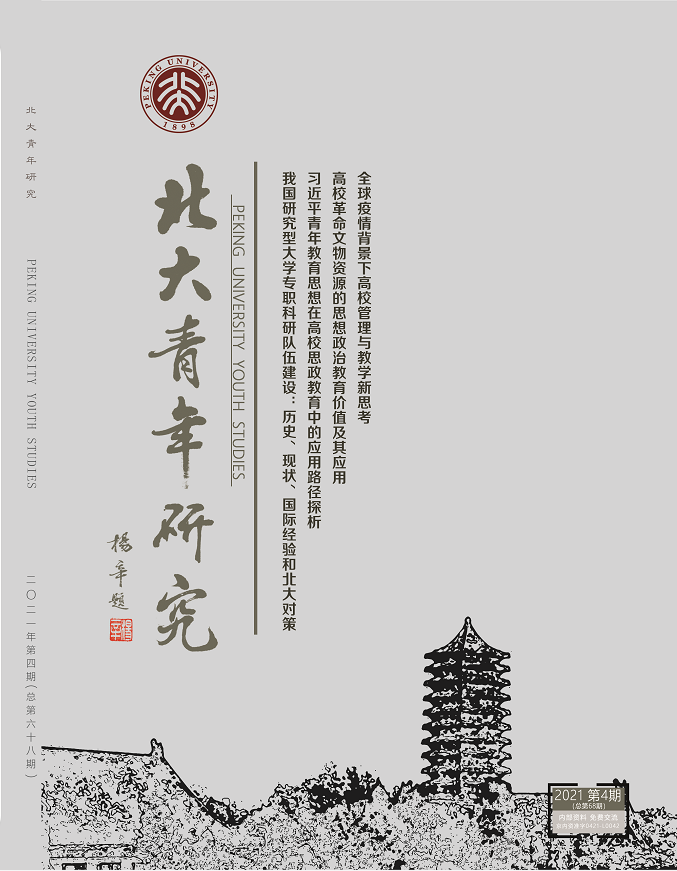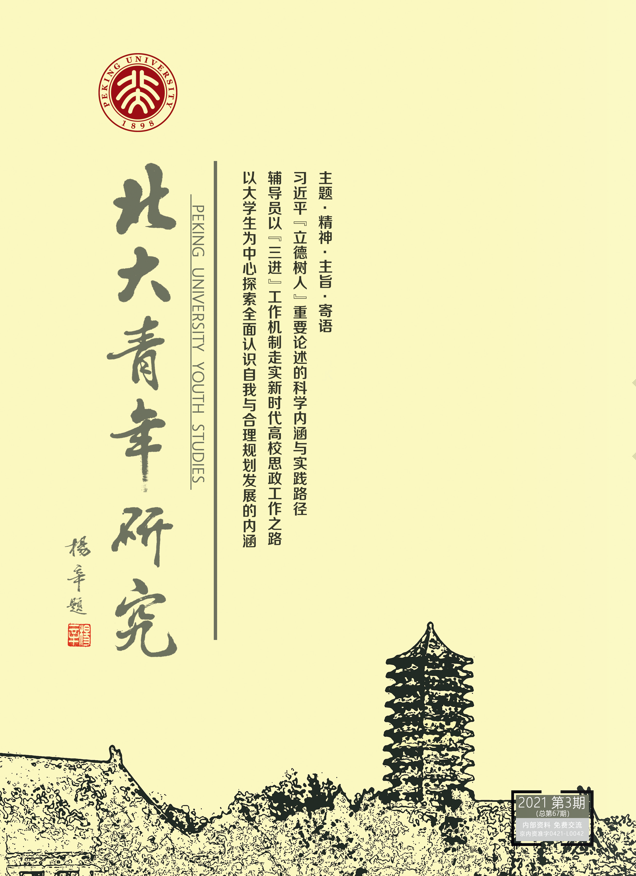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青年同学向老一辈学者学习什么? ——祝贺张世英先生九五寿诞感言
最近,北大哲学系与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全国范围的庆贺张世英教授九五寿诞的学术研讨和祝寿会。北大哲学系现离退休教师40多人中,80岁以上者20多人,90岁以上者2人:张世英,95岁,西方哲学著名专家兼美学家;杨辛,94岁,美学家兼著名书法家。目前,他们的身体强健,精、气、神更佳。两位教授早已越过“米寿(88)”,对他们都可相期以“茶寿(108)”。两位教授的如此高寿,是与他们的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哲学与美学修养密不可分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大学里的哲学系,只剩北大一家,不少大学的哲学精英大都集中于此。名师汇聚,可谓盛极一时。比如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洪谦、唐钺、张岱年等。几十年来,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诸多磨难,后来回到学术家园,又多半笔耕不辍,硕果甚丰。其中冯友兰先生,在85岁至95岁高龄期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巨著,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之所以都能寿过耄耋之年,就在于他们原本就学识渊博、功底扎实、胸怀开阔。他们在经受各种磨难之前,已经不同程度地做成了学问,或者说,他们已经具备了某种天然的秉赋和素养。冯友兰先生经受的磨难,是比较多的。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坦陈自己的心态时,却轻松、自然地背诵了禅宗六祖惠能的一段“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种与天地一体、处乱不惊、泰然自若的精神境界正是他度过难关的支撑力量。
这里想着重谈谈张世英先生。与上述老一辈学者相比,张先生的治学生涯略晚一些,但他自幼受家庭良好教育的熏陶,养成“少无适俗韵”的性格,立志“做学问中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又深受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吴宓等一大批一流名师的教益。在学术自由的浓厚氛围中,他从经济系转入哲学系。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只能在茶馆中读书。他攻读原著,刻苦钻研,奋力吸取人类思想史上的各种智慧。汤用彤先生曾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的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这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北大校长,从蔡元培、胡适到马寅初、汤用彤,都有这种“大家气象”。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扬这种“大家气象”。他认为,北大不仅应名家辈出,而且应学派林立,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和“大家气象”。
张世英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和老师。他的治学生涯虽有一定曲折,但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主要指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文化大革命”前,他的研究和讲授,重心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他开设了很多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课,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是多方面阐述黑格尔思想。我们知道,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思想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涉及面很广泛,内容相当丰富而深刻,但又极为晦涩难懂。对于初学者来说,开始接触这类著作,多半像读“天书”一样。张先生的讲课起着解读和引领的作用。他出版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自我实现的历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对广大师生和普通读者读懂、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帮助。黑格尔又是西方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辩证法理论集中在《逻辑学》中阐述。对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张先生是下过大功夫的。我在上学期间并未听过他的课,上世纪80年代我才有机会听他对本科生讲的“黑格尔《小逻辑》”。对于乍一看去会感到十分抽象和枯燥的著作,张先生由于掌握丰富材料,又善于结合现实生活,能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把黑格尔《小逻辑》中的一系列层层推进的范畴,梳理、讲解得十分清晰。听后茅塞顿开,获益良多。他专门出版了《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等著作,发行量很大。应当说,解放后国内关于系统研究和讲解黑格尔哲学的方方面面,其成就之显著和影响之广泛,无疑首推张先生。
随着时代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张先生的哲学活动也有过重要的转向,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是国内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张先生虽然继续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但他开始从立足于西方主客关系视角的传统形而上学,转向立足于人与世界相融合的生活哲学。这就使他从西方传统哲学进一步升华到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哲学,使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对接,使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等著作中。从此,张先生的哲学研究,便从哲学进一步扩展到美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等领域,力图超越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在2011年出版的《中西文化与自我》中,他经过中西两种自我观的比较,鉴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别人的依赖和对自我的根深蒂固的约束,他主张吸收西方人“独立自我”的观点,并从民族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概括个体性逐步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寻求中华文化未来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张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年里,逐渐形成的新哲学观,意在引导人们超越主客体关系,上升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并把这种精神境界视为最高层次之美。这样,从哲学到美学,张先生试图依据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学说,以及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参照西方现当代或所谓“后现代”美学中有关人与世界相融合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若在现实生活中得以现实化,使人们获得的自由便是具体的。类似于海德格尔把自由之境界定为人生的“本真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由此提出审美的“神圣性”观念,张先生给以肯定和发挥。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哲学导论》和《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二书都涉及人生的精神境界。精神境界问题是人生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多次讨论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以古典诗词比喻学者治学的三种境界。中国哲学专家冯友兰在《新原道》中划分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于这个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有人可能感到难以把握,有些可望而不可即。张先生提出的人生四种精神境界则是: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他认为这种理想中的“审美境界”意味着“把人生的最高境界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历世俗各种对立面的磨炼,却仍如荷出污泥而不染,海纳百川成汪洋。”因而“是一种经得起磨炼的蓬勃奋发、博大高远之境”,它“既是入世的,又是超越的。”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先生的学术成果愈来愈显得成熟,愈来愈富于开创性。就拿《哲学导论》来说,近些年来,突破长期形成的课程框架,哲学系为一年级新生开设了“哲学导论”一课,也曾作为全校“通选课”开设。先后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叶秀山、余敦康、张祥龙等先生讲授。他们各有所长,普遍受到欢迎。张祥龙先生的课更是场场爆满。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写出和出版新教材。唯独张世英先生的课,不但效果很好,而且及时出版了《哲学导论》这部精品教材。记得在此之前,有青年朋友要我推荐国内的哲学读本,我很难找到一本合适的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虽种类、版本众多,却感到越编越不如人意,因大多不是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我只好推荐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的智慧》、美国学者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及海外学者所著《哲学概论》之类。后来我便推荐张先生的《哲学导论》。读者的反映是:内容丰富、思想新颖、作者有独到见解。当然,不必为尊者讳,初学者中也有人反映:不太好懂;文字上有的句子太长,有略嫌艰涩之处,似不如冯友兰 、朱光潜、方东美等先生的文字那样行云流水般地顺畅、自然。另外,书中阐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历史观等部分,没有专论当代哲学讨论较多的价值观,似略嫌不足。
哲学是启迪和运用智慧的学问。当前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普及性、启蒙性的哲学读本,对于广大读者,提高哲学素养和审美境界,思索和理顺人生根本问题,实属急需。从这个视角看,《哲学导论》似尚有进一步提炼、加工的空间。
综观张先生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无论在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方面,都成就卓著,而且越来越富于开创性。张先生的治学经验与方法,有哪些显著特点,特别值得青年同学们借鉴与学习呢?
第一,勤奋于攻读经典文献。在哲学与人文学科上,要卓有成效地作出贡献,在天赋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个人的勤奋自学,刻苦钻研。所谓“天道酬勤”是也。个人的功夫又要着力于中外经典文献上。只有经典文献才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人类智慧的成果,是寻真问道的缘由。因此,攻读和熟谙经典文献,力求融会贯通,是在治学上登堂入室的必经之路,舍此并无其他捷径。如果轻视甚至舍弃这个方面,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所谓“杰出人才”或“一流大学”,只会流于空谈。张先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便熟读若干儒家经典,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条件极其艰苦简陋,他主动接受名师指引,利用茶馆自学,熟练地掌握了两门外语,攻读了一大批中外经典,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并且他善于利用政治运动的间隙读书或写作,比如,利用“文革”期间“病休”的机遇,阅读和背诵大量唐诗宋词,比别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平时在家里他也很少闲坐,每日外出散步时都在思考哲学问题。进入耄耋之年更显得思想活跃,新见迭出,文如泉涌,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世英文集》共十卷。这并不包括他的全部著述。这种始终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研究的风格与习惯,正是他的学术成就卓著,身体素质强健的基本原因,这首先十分值得青年同学们学习。
第二,力求中西融合与会通。张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就熟读、背诵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以及古典诗词,奠定了古文与国学的功底。就读西南联大时,从经济系转入哲学系,在许多名师指引下,在中西哲学、文学与外语等方面夯实了基础。因此,他一开始从事教学与科研时,便如当年蔡元培评价胡适所说:“中西俱粹。”这样他便视野广,思路宽,容易触类旁通,有利于中西思想的比较与融合,进行综合创新的思考与研究。这是老一辈学者的共同优势。张先生虽起步略迟,却完全继承和保持了这个优势。这是当前我们这些教师所最缺乏的。如果长期缺乏这种功底,也不打算进行基本功的训练,那么“杰出人才”或“一流大学”的目标,势必流于空谈。
第三,占据学科领域的制高点。在学术研究中,占据什么位置直接关系到学术的水平与成就。不论是哲学还是美学,不论是西学还是中学,张先生总是占据高峰,把握学科领域的制高点。他首先集中把握与突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对于中国哲学,他主要把握老庄哲学,集中运用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美学领域,他把握西方当代最新思潮,或所谓“后现代”的美学思潮。正是“登泰山而览众山小”。这便有利于他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式地分析、评论各种思想,提出综合创新的见解。这种治学的气势与方法上的优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第四,开展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张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后期的开创性探索,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在我看来,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短短八年内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关键就在于弘扬了这种传统。这正是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是西南联大在办学育才上创造“奇迹”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因。没有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就没有学术上的真正创新。张先生由于继承和坚持了西南联大的学风,才有今日一系列的创新见解与成果。应当看到,也并不是每一个西南联大毕业的人,都能坚持这种学风的。因为这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学术研究中也需要一种审美的境界。当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比较普遍地存在某些依附性,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是学术上的致命伤,只有坚决克服学术上的各种依附性,做到不依附于私利、不依附于权威、不依附于他人,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探究,才能促进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才能有真正一流大学和杰出人才的出现。
① 张世英:《美在自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