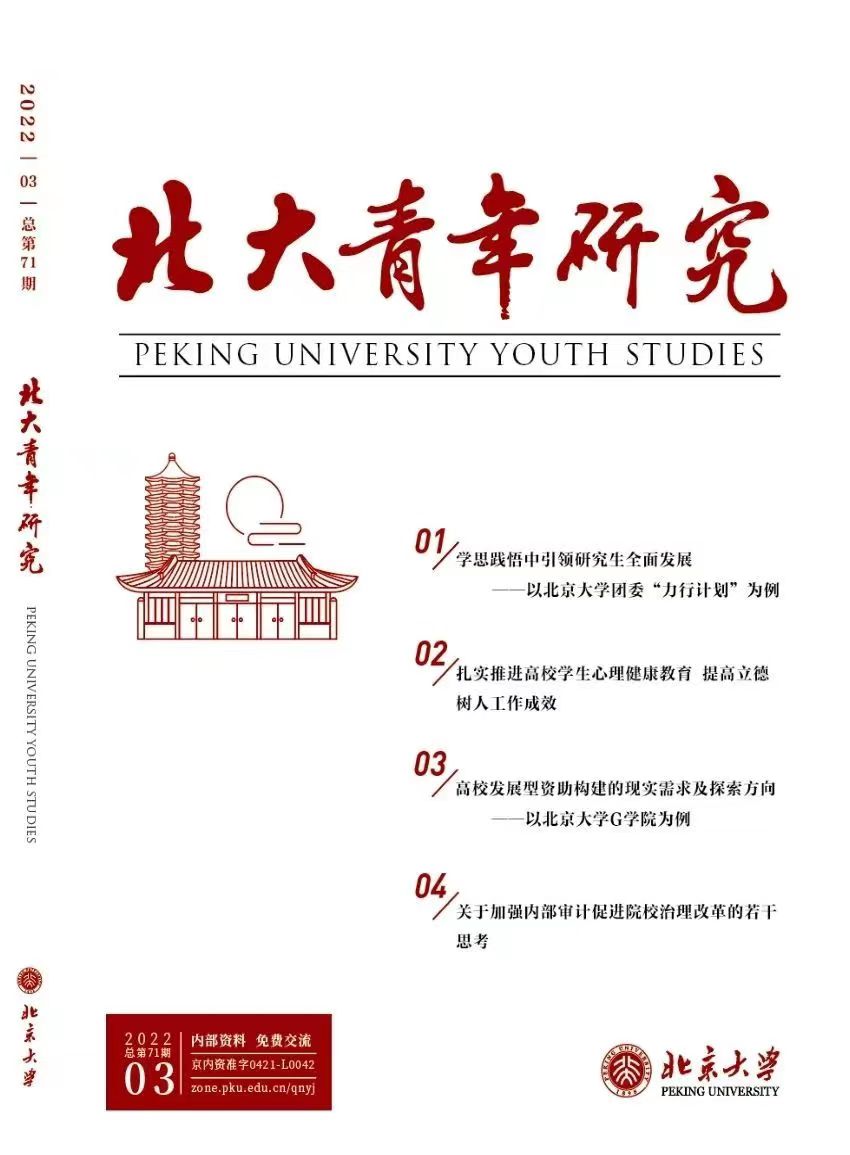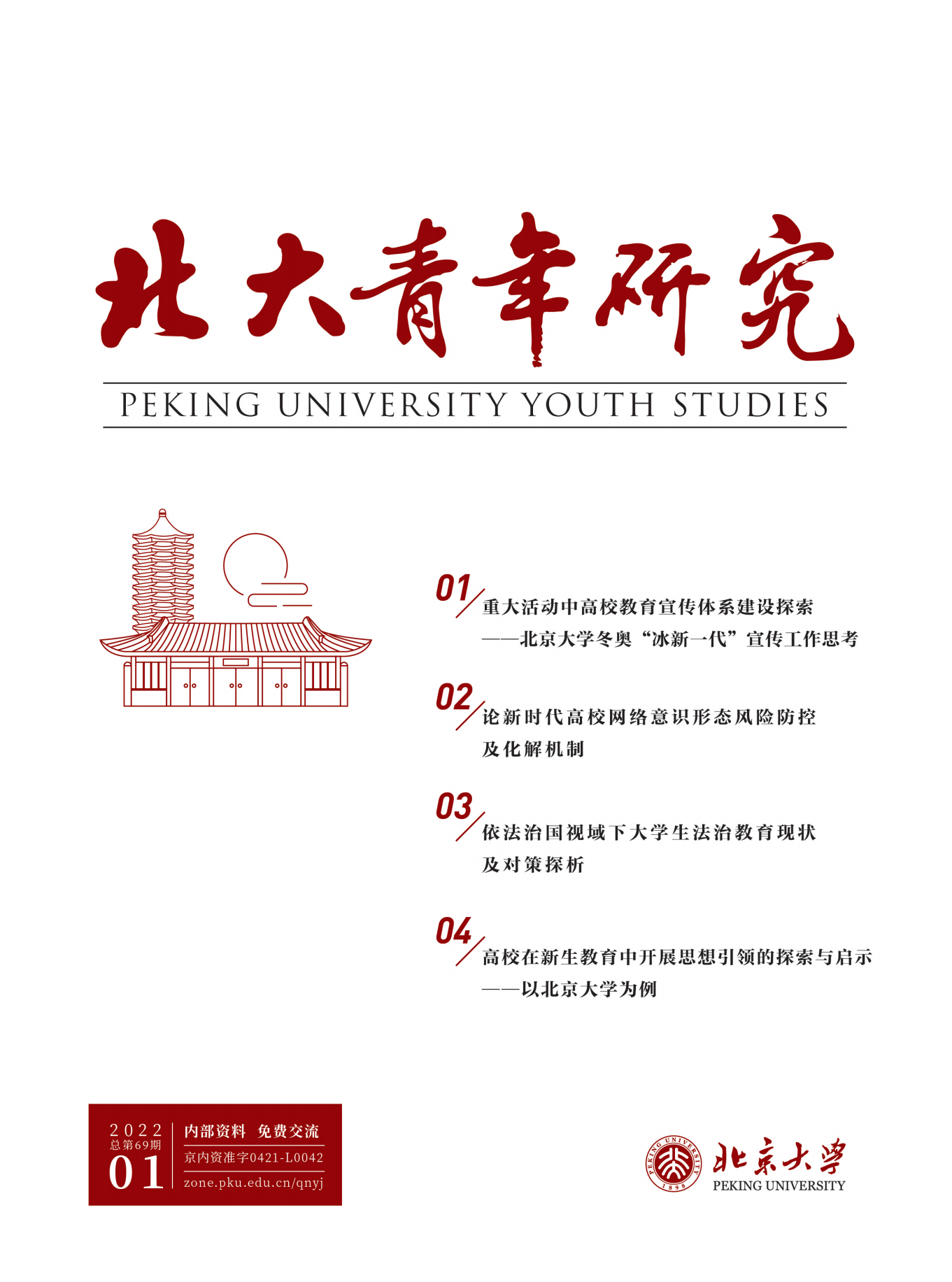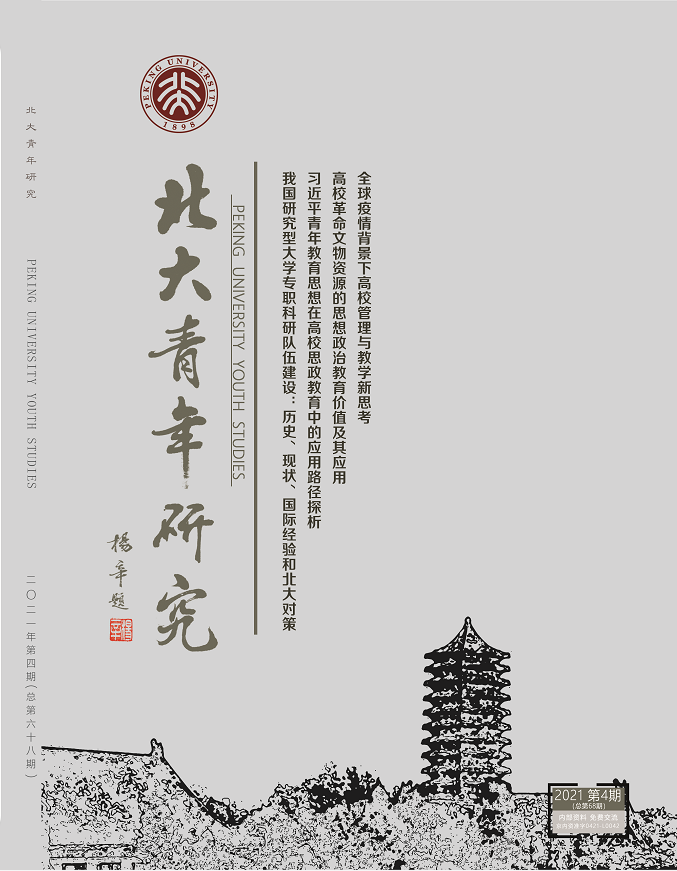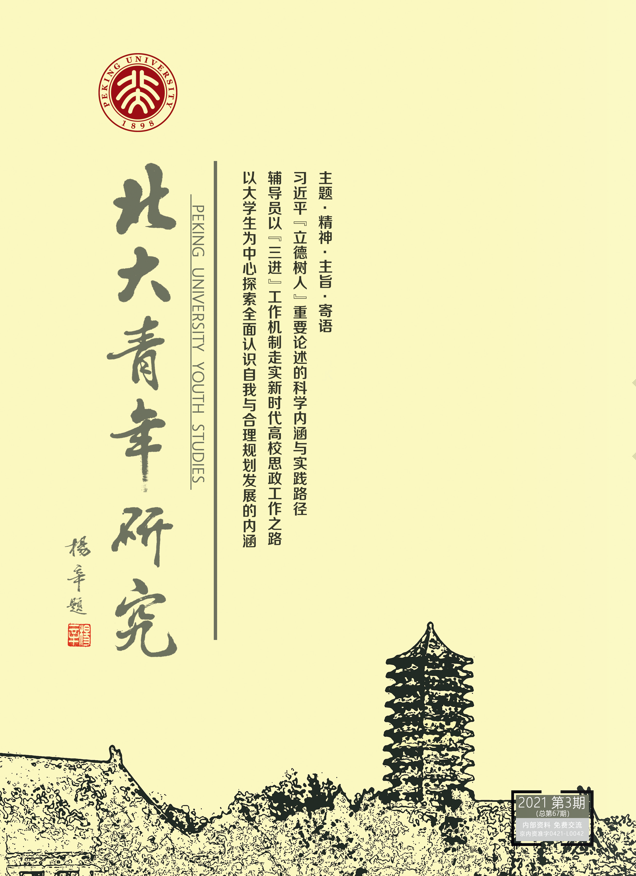刍议“学术至上”与北大精神
作者:任一丁 任羽中
发布日期:2013-01-14
摘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文对北大传统的塑造极为关键,重读此文,并梳理其历史脉络——包括蔡元培留学经历、在北大的改革实践、当时北大的学风校风,以及学生运动与蔡元培的互动关系等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以“学术至上”为核心的北大精神。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精神;学术至上
一般认为,“北大精神”当然与开风气之先的蔡元培校长有关。但事实上,“北大精神”的最早提出者,却应该不是蔡本人。这个词或可追溯到蒋梦麟《北大之精神》一文,时任代校长的蒋梦麟总结北大每在“一致的奋斗”中都能收获成功的经验时,把原因归结为北大“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①]。两年后,鲁迅在《我观北大》中说,虽然中暗箭、背谣言,“北大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②] ;四年以后,马寅初在杭州校友集会上作蒋梦麟的同题演讲,感叹“北大形质暂时虽去,而北大之精神则依然存在”,而这种精神,就是“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牺牲主义”[③]。
今日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中国思想界还就此发生过针锋相对的争论。无论后人如何阐释,要真正理解北大精神,必绕不开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改造和办学实践,是他奠定了北大精神的“底色”。
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深受德国影响。蔡元培曾先后三次留德,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时间最长、工作学习最投入的第一次[④]。1907 年,当时翰林院公费官派留学受资金限制,名额有限,又以东洋日本为主,蔡抱定“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的决心,负笈西去,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在柏林过起“半佣半丐”的勤工俭学生活,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著文编译,又给唐绍仪的四个侄子教习国文。有了一定的积蓄后,他才得以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千辛万苦,一朝圆梦,蔡元培对学习机会自然珍惜备至。他孜孜以求、博览群书,特别留心于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等文章中,他多次提到德国大学的理念和体制,并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在所译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中,大学教育的“德国模式”被概括为:“研究科学之试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⑤]包尔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蔡本人的认识。蔡后来主政北大,其治校的核心理念即由此确立。
蔡元培接手北大时,北大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大都有着极强的功利心态,“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构,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者,可为毕业后奥援也。”这种攀附结交的功利思想,甚至比“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本位思想更有所不如。罗家伦是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入校的,对当时的学习环境有一个很真切的体会:“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⑥]
蔡元培深刻地意识到:北京大学被谤为“赌窟”、“探艳团”、“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虽然只是个别群体的个别现象,但学生怀揣“官本位”思想以及私德有亏,显然对大学的学术风气有强烈侵蚀。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以三事为诸君告”:首要的是让学生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其次要品行谨严、“砥砺德行”;其三要敬爱师友,以小节开创良好校风。其实,就后两条而言,无论是砥砺德行,还是敬爱师友,都是对研究学问这一基本宗旨的保障。而修身之目的,还是治学。蔡元培之所以要疾呼以“进德会”之旨趣来重建北大的良好形象和学风,原因也正在于此。而德行既兴,纲常既振,敬爱师友固然不是问题,学术环境自然也就蔚然可观了。所以,上述三点归根到底,都是为着研究学问这个目的去的。
蔡元培基于“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的判断,要求学生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的精神孜孜求学。
蔡元培针对学生“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尤少”的状况,把他留学所得的这套重视研究和教学的“德国模式”搬到了北京大学来。
第一,就是拿学科设置开刀。蔡元培在1918年初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改制议案,即《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直陈其时教育体制中重复办学和资源浪费之弊,“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蔡元培主张学习德意志“既有高等专门,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专设并扩张文理科,把商科降为法科分支,以法科预备独立,并停办工科,转入北洋大学,把北洋大学的法科转入北大。
扩张文理、偏废法商的“大文理科”主张,在蔡元培“学”“术”之辩的问题上可见一斑。蔡元培认为,“文理,学也,……法商医工,术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⑦],这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不学无术”的观点实际上包含了对“大学何为”这一根本问题的高下之判,也在无形之中深刻影响了北大百年学科发展的方向。
第二,聘任师者“以学旨为主”,言行举止思想派别方面并无更多别的要求,以贯彻“兼容并包主义”。虽然蔡元培把上海“进德会”引入北大红楼作为师生规诫,但那只防小人不防君子,对于“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的人,只要不荒废教学研究,不引诱学生,则听之任之。至于“新帝制派”的刘师培,“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政治“反动”者辜鸿铭,只要讲课无涉政治,则更无甚关系[⑧]。而事实上他们也确未讲过一句帝制,一句复辟(据罗家伦)。学问多寡、教学勤懒成了衡量师者的唯一因素,此外种种,都可以放任自由。由此可见,后来为人称道的“兼容并包”,原是相对于“学术第一”的先要条件而言的,没有“学术第一”这个大前提,就谈不上“兼容并包”。
在每年例行的“开学日演说词”上,蔡校长都会呼吁教员、学生专心研究学问,表述也几乎一模一样[⑨]。“五四”之后,这样的劝勉更是几乎每文必谈。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实在与蔡校长的期望不符。原因也很简单:外敌入侵、国家危亡,北大与北大学生,当然要奋起救国救民,哪里还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个角度讲,爱国师生将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当然是正义、正当也不得不如是之举。
不过,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北大当时被裹挟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的洪流中,许多学生未必没有“社会活动家”、“救世主”的精英意识。傅斯年便对当时北大的学习风气有一个概括:“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仍是议论之风气,非讲学之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⑩]无独有偶,罗家伦在后来回忆自己求学北大时,对“自由讨论的空气”颇为留恋:“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当时大家称二楼这个房子为群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堂,一楼那座房子饱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堂。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11]。“言不及义”、“无所用心”固然是文人自嘲自谦,但仔细品味,未尝不能品出一点“名士”优游的优越感。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他在五四运动后去职南下,劝告全国学生回校复课,“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不要停课闹革命,纠缠其间荒废学业,而唤醒同胞,“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12]。
“五四”之后,学生运动已成绵延不绝之势。蒋梦麟先生对蔡元培的态度有一个判断:“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后来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13]蔡元培是否因为学潮而去职尚无定论,但他一再强调并维护的大学学风,就这样面临危险的边缘,以至于回任北大校长时,一定要拿出他的德国经验劝导学生:在外国多年,并未多见罢课的事情;并劝慰学生“目的达到,可以安心上课了,……不要再为校长的问题分心”[14]。
此后,蔡又向学生提出“读书救国”的忠告。当时即有学生撰文回应,明言并非不愿“有充分修养,以备将来救国”,只是时势并不容许:“兵匪遍地,内战不息;多数学生的家庭状况,日趋破落衰败;教育经费克扣殆尽,不良教员充盈,多数学校沦于倒闭之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纵然希望潜心读书,也是办不到的。在参与运动的学生看来,“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全体民众一致奋起尚且不遑,学生岂能埋头书本,不问国事”的社会现状已经构成学生运动合法性的理由,而“安静读书、以备将来”之说则是“段祺瑞、章士钊及各省军阀、教职员所用来镇压学生运动,早为东交民巷诸列祖列宗所拍掌叫绝的符咒”,断无服从之理。[15]
蔡校长的苦心孤诣和坚毅执著,在当时或不合时宜,也无法施行,但长远来看,这种“学术至上”的价值取向才真正构成了“北大精神”的核心。近百年来,北大虽然历经风雨,但“学术至上”的精神一直传承不绝,历久弥新。在2012 年6 月召开的北京大学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党委书记朱善璐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他对蔡元培校长的一次校庆演说作出了历史的回应:
九十五年前,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未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惜我国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耳”,表达了与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平行之发展”的强烈愿望,也发出了无法实现之慨叹。再过五年多时间,就是蔡元培先生发出这慨叹的一百年了。
今天,可以告慰蔡元培先生与北大先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这一梦想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成为了国家战略、民族工程和世纪规划,并且正在加快推进。百年期盼,世纪梦圆。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力争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一多少代北大人的光荣梦想,将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成现实。在此基础上继续奋斗,我们还将在不远的将来,让一个充满活力、享誉世界、有更高发展水平的北京大学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我们的人生何其有幸,我们的责任何其重大。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这段话,既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时代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北大人应该真正把“学术至上”的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如此,才能圆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才不致辜负了北大的先贤们。
作者简介:任一丁 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任羽中 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①] 最早发表于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②] 最早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③] 马寅初于1927年12月20日在北京大学29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词,由沈文笔记,首刊于1921年12月21日《申报》。
[④] 蔡元培在第二次游学德国时,曾用“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表述自己的生活状况。据《蔡元培传略》。
[⑤] 该文是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部分,经蔡元培翻译后,最早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
[⑥] 罗家伦:《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总第324 号,1931 年8 月26 日。
[⑦] 蔡元培:《读周春岳君< 大学改制之商榷>》,《新青年》第四卷第5 号,1918 年5 月15 日。关于蔡元培“学”与“术”的问题,哲学系胡军教授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胡军:《北京大学精神的一种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4 期。
[⑧] 以上参见蔡元培:《致< 公言报> 并答林琴南君函》。
[⑨] 如《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又如《北大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至于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但能图得生活上便利,即为已足。”《北大一九二二年始业式演说词》中,甚至有“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的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这样的概括。
[11] 罗家伦:《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与五四运动》。
[12]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首发于1919 年7 月23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21 号。
[13] 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详见《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 年。
[14] 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词》,首发于1919 年9 月22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43 号。
[15] 牧武:《学生与救国运动——敬质蔡孑民先生》,收录于《中国学生》第18 期,1926 年3 月6 日刊。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考证,“读书救国”被视为“反动派”对付学生运动的四种方法之一,详见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88 ~ 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