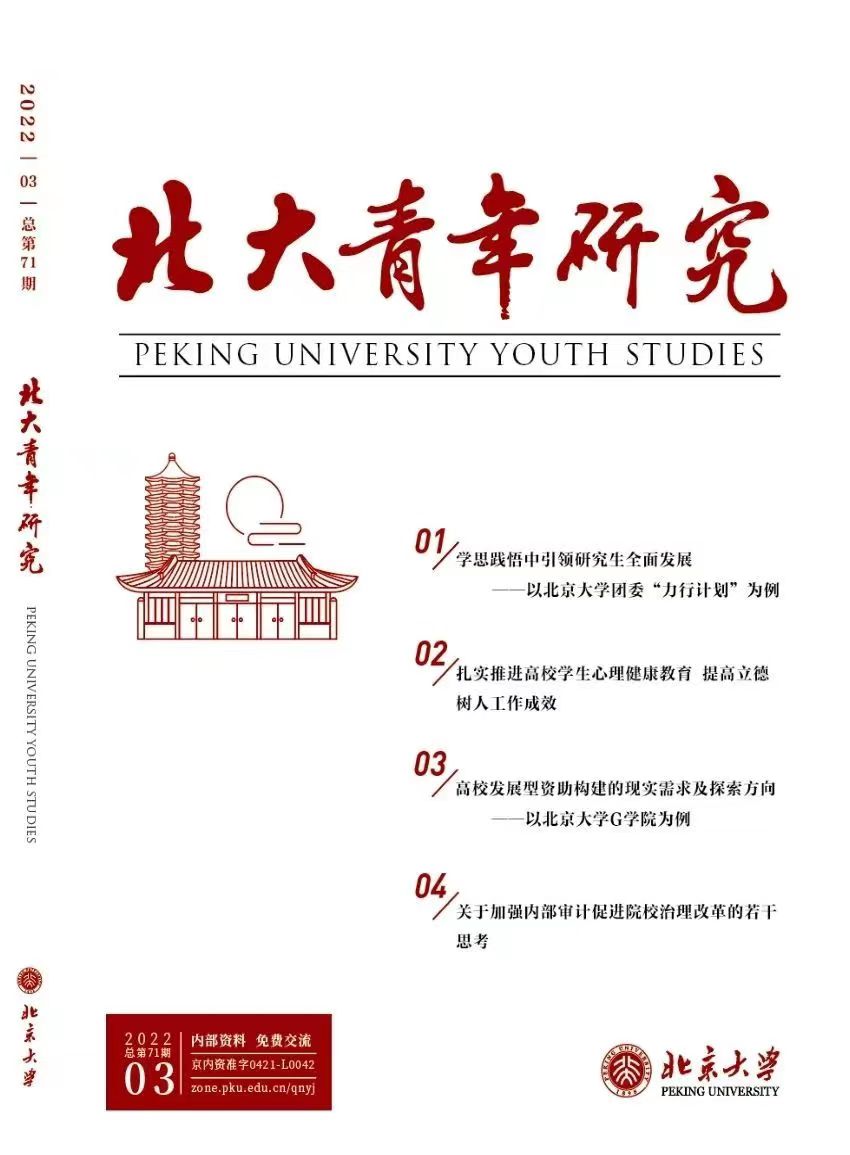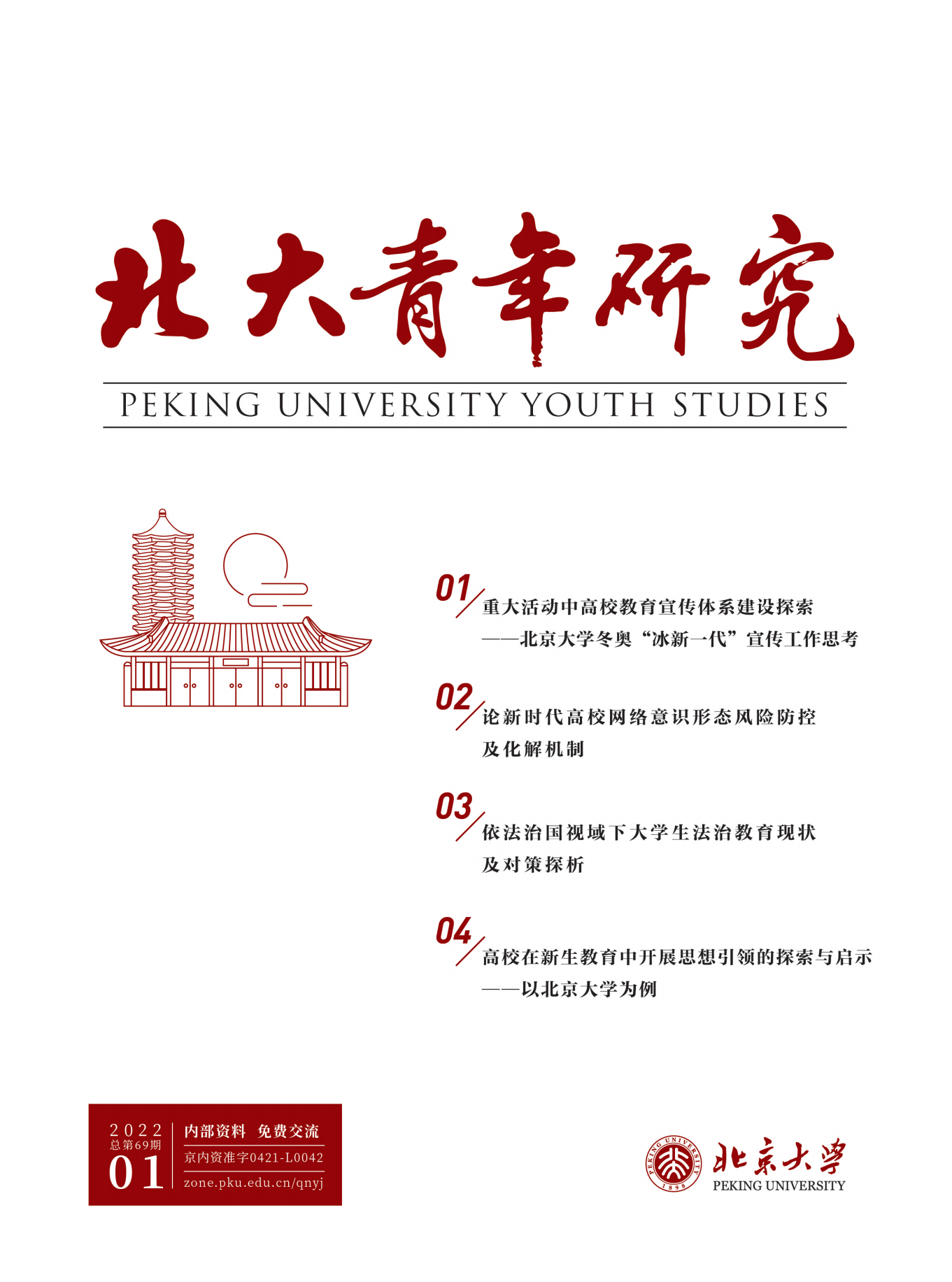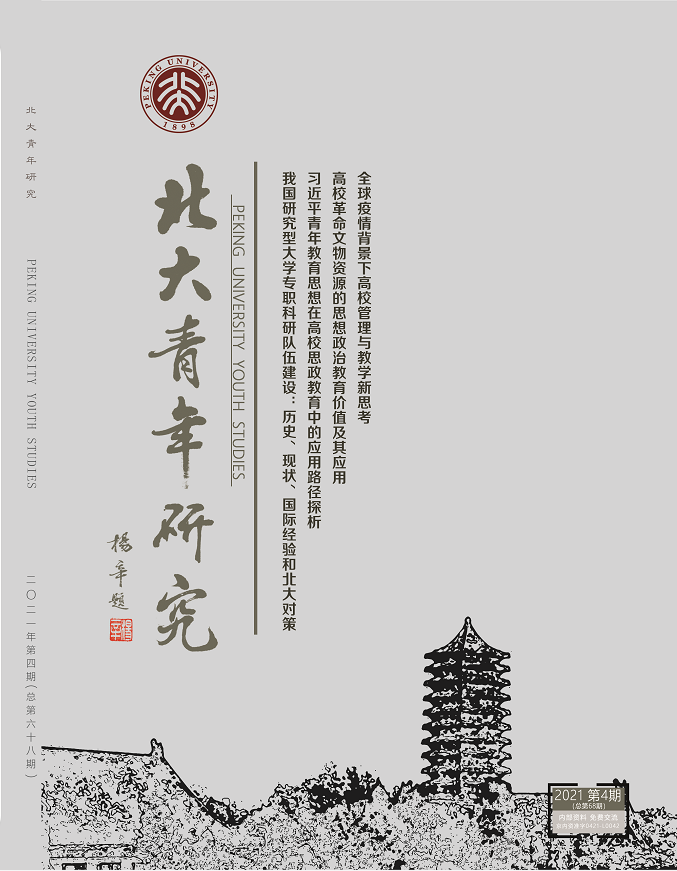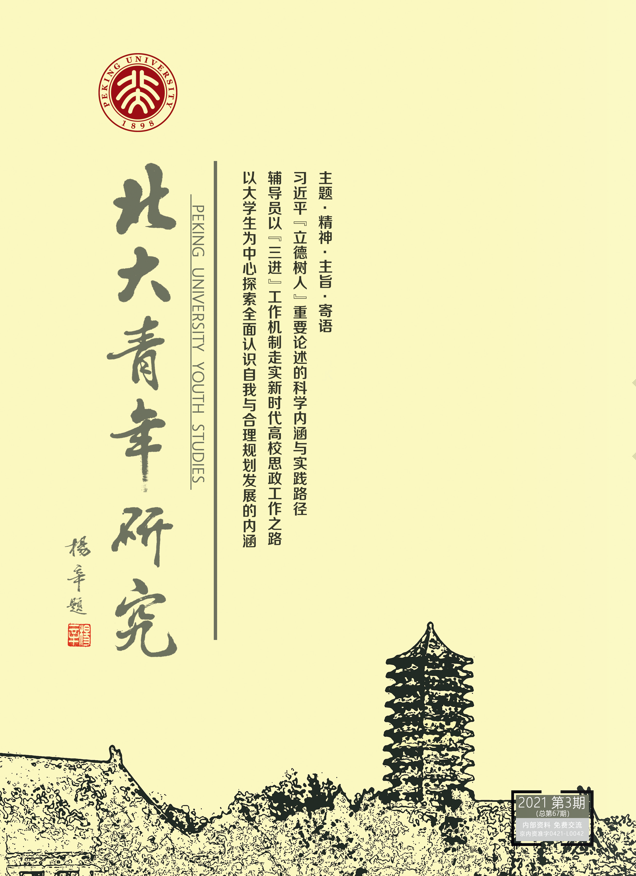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作为一个语词和一种文化现象的“山寨”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来流行于互联网的“山寨文化”源流的梳理,将“山寨文化”放在新世纪网络文化的发展过程,尤其是网络语言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进而分析了“山寨文化”背后的某种当下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现象。
关键词:山寨 网络文化 大众文化
2008年被《南方周末》的年度文化盘点专刊称为“民间语文中新单字持续井喷”的一年[1],从这个角度来看2008年的网络文化,绵延了数年的对“网络语言”的讨论似乎在2008年具有了另一种意义。《新周刊》283期的专题《我被你雷到——多元时代的雷文化》对近年网络文化的面向,以及网络流行语有一个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这种轰轰烈烈“网络造词运动”恰恰可以对罗兰·巴特在五月风暴“幕落”之后的激进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做出一个充分中国的和当下的回应。而其中“山寨”一词,却因其充分后现代的特征和与现实的紧密关系而溢出网络,甚至进入被央视等主流媒体和政协提案讨论的语境,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面向。
“山寨”一词,本义无非就是“山区村庄”和《水浒传》式的“占山为王”。2008年里,“山寨”一词却从“山寨手机”一路扩展到“山寨春晚”,这个词因而也具有了“低劣模仿”的含义。有趣的是当这个词从对制造业描述转入大众文化领域之后盛极一时,由此也印证了当下中国网络文化的某种机制。
一、一个命名:从“山寨手机”到“山寨文化”
“山寨手机”并不是最早的“山寨”工业品,实际上多年前从方便面到洗衣粉,“山寨”品都比比皆是。曾有网民撰长文并配图总结各种“山寨”品牌,如“周佳牌洗衣粉”之于“雕牌洗衣粉”或者“康帅博方便面”之于“康师傅方便面”之类。自然那个时候这些东西还被称作“假冒伪劣”而并非“山寨”,只是在“山寨手机”被广泛关注之后,它们才获得了“山寨产品”的命名。而其中的有趣之处是“山寨手机”并非被作为假冒伪劣产品对待,2008年关于“山寨手机”的入网问题还引起了很大范围的争论,而在这之前,“山寨手机”早已因其不亚于,甚至远胜于品牌手机的功能、设计和低廉的价格实际上占有了大量市场,并且获得了“山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辨识性的命名。
稍作梳理就会发现,“山寨手机”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性”来得实在有趣,因为这些“山寨手机”事实上与 “山寨”洗衣粉或者方便面没有本质区别,但获得的对待却完全不同。原因显而易见,“山寨”洗衣粉与品牌洗衣粉的价格并不会差太多,但“山寨手机”往往能有千元左右的价格差;而同时,手机在当下中国已经近乎必需品,由此带来的大量需求使得“山寨手机”得以生存,进而获得发言权,甚至向品牌手机叫板的权力。“山寨”作为一个对“文化”的命名所具备的某些特征便由此彰显。
第一个用“山寨”来描述网民的戏仿行为的人无疑是富有智慧的,而这个语词本广泛使用也说明它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获得了认可。“山寨”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展到“草根”对“主流精英文化”的有意识的滑稽模仿,并由此对其进行消解和娱乐。
在较早一批对“山寨文化”进行讨论的文章中,网友“逆转录猴子”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2]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这篇文章借美国青年Steven Zuckerberg的视角,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山寨现象”早就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之中,只是最近才获得命名。文中一些观点非常尖锐,比如:“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以及“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逆转录猴子实际上指出了“山寨现象”正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某种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处境。这篇文章曾以《美国青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的题目被广为转载,并引起了激烈争论。而80后作家韩寒的文章《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3]的观点更加有趣——“我们的国家建国初期就是山寨苏联”。实际上就细微的语义而言,“山寨”在如今已经是“模仿”的同义词。
这两篇文章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逆转录猴子和韩寒都敏锐地指出了“山寨”作为语词的实质——对早已存在的现象的命名,以及这种命名的蔓延;同时他们也谈到了这种命名的荒诞性——一朝“山寨”则处处“山寨”,以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从而指出了“山寨”这个语词之中的裂隙。
二、一个语词:作为网络语言的“山寨”
在对“山寨”作为语词进行了梳理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山寨”的意义,以及这个语词盛行一时的原因,并不来自它指称的现象,而实际上仅仅是来自这个语词本身。换言之,重要的不是什么现象是“山寨”的,而是把什么现象叫做“山寨”。最初“山寨”还被用来描述恶搞或者戏仿,这是从周星驰到胡戈的一个网络文化的脉络,而后词义扩大,最终成了现在所包含的“模仿”和“非官方”特征的一切现象。而更加有趣的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许多网络文化现象都以“山寨”自居,无论是在《赤壁·下》上映之前的自拍搞笑“山寨《赤壁·下》”,还是“山寨百家讲坛”或是“山寨春晚”,“山寨”成了某些互联网文本的自觉身份标识。
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至少包含两条脉络,其一是从“芙蓉姐姐”以来,网络文化中以“出位”而“出名”的脉络,上自木子美,包括胡戈,甚至最近的小沈阳,都可以归到这个脉络之中,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出位”都是靠“搏”而获得的,换言之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新周刊把这种行为成为“贱文化”,意指在网络传播中“制媒”一方有意识地制造注意力。而2007年以来的“雷文化”则被认为是传播中受众一方有意识地对意义进行消解,对信息进行斯图尔特·霍尔意义上的“对抗性解码”[4]或者“游戏性解码”。那么“山寨文化”实际上是在这个脉络上,制媒者与受众的一次合谋:制媒者有意识地采取一种消解和戏仿的编码方式,而受众一方却是无障碍的解码——在“雷文化”的语境下,“山寨文化”毋庸置疑地成为“雷”的最佳阐释。于是,在霍尔的意义上这种编码-解码的过程却成了“主导性符码”,也即意义的充分传达。这就成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因为在霍尔那里,“主导性符码”实际上是一种获得了霸权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而在“山寨文化”之中,无论是制媒一方还是受众一方,显然都不具备这种特性;而事实上充分传达意义的编码-解码过程则带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主导权或者文化霸权——一种显然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可以交流并充分传播的共识,这或者可以被称作是某种“网络舆论”。
第二个脉络则是网络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个脉络可以从《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包括火星文,以及所谓“BBS文化”。而2008年井喷式的网络语言,包括“囧”、“雷”等单字,“山寨”、“散步”等词以及“正龙拍虎”、“秋雨含泪”等“成语”[5],在这里语言成为一个创意的竞技场,表达方式的层出不穷使得互联网成为中文写作最具原创性的场域。著名诗人胡续东称:“网络流行语正是未满百岁的年轻的现代汉语自身活力的体现,即使稍显突兀,也不过是年青人脸上的青春痘而已,它反倒有力地证明了现代汉语还处在活色生香的青春期。……网络流行语从编码方式、修辞手段和衍生复义迷宫的炫智诉求来看,完全是高段位的文学语言创造力在更为日常化的网络和大众传媒情境中的延伸或变形。”[6]在笔者看来,网络语言的显著特点是表达强于意义,形式大于内容,使用者们更看重的是身份标识和某时尚的感觉。于是“山寨”一词的风靡一时由此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它充分的娱乐和时尚,因为它是2008年度流行语。
三、一种指认:“山寨”折射出的某种“舆论”面向
“山寨”的强势在于可以用它来命名一种“文化”,这与所谓“贱文化”和“雷文化”,乃至往前追溯的“非主流”和“火星文”都是不同的——在于其作为一个对网络之外和网络之中诸多事实充分而有效的“命名”,值得注意的正是“山寨现象”并不仅仅指称文化现象,而包括了社会经济的诸多面向——这是其他网络语言所不具备的。正如前文所述,“山寨”产品因价格和必须程度不同,其“正义性”是不同的,这就反映出了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之后作为“世界工厂”的另一种面向,尤其在服装和电子产品方面:“山寨”的耐克或者阿迪达斯,以及“山寨手机”,事实上昭示的是全球工业体系中被剥削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这种意义上的“山寨”产品实质上是去掉了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带来的高额附加值之后的工业品。在这个意义上,“山寨”一词实际上回归了它的本意——《水浒传》里“占山为王”的目的最终是“受招安”,也就是从山寨做起,最终还是要回归“主流”的商业模式。
从这个思路来看“山寨文化”,一个明显的误区是认为“山寨文化”是在“对抗精英文化”。细数那些“被山寨”的原始文本,无论是周杰伦还是百家讲坛,抑或新闻联播或者春晚,无一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众文化”,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山寨是草根对精英的胜利”之类的观点呢?回头看一下那些“山寨”工业品,显然“被山寨”的产品没有一种属于真正的奢侈品,而实际上都是大众消费品,“山寨文化”所“山寨”的对象也并非真正的精英文化。那么我们需要处理的正是这种对“精英”的想象和指认。如果将春晚和百家讲坛指认为精英文化,那么与其说是针对这两个节目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媒介——中央电视台——象征的话语权力,而对它们进行的“山寨”式的消解正是对话语权力的消解和颠覆。如果将周杰伦章子怡之类明星指认为精英,实质上是将明星象征的名声和资本指认为精英。更加有趣的是,在“山寨”的命名中,并不包括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的十足的“山寨”版本,相反它却被作为最成功的“本土化”案例。相同的行为为什么获得不同的命名?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网络舆论将大众文化指称为“精英文化”,实际上是将一切与资本、产业联系的大众文化工业都放在了他们所谓“草根”的对立面。如果回到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讨论中[7],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今的中国网民事实上具有了对“文化工业”的某种判断——意识到了文化工业试图建立的主导权。这种判断并不是来自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机制的自觉,而是来自被互联网改写的社会结构——发言成本被充分地降低,于是一些被遮蔽的东西通过“山寨”的命名浮出水面:作为大众文化的受众的“大众”们言说和表达的要求。相对大众文化的制媒者而言,受众显然处在一种表达和言说的弱势地位。
所以这就真正揭示了“山寨文化”的实质。当一个网民将自拍短片命名为“山寨某某”的时候,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某种崇拜——不然不会进行模仿,哪怕是如此粗糙和滑稽的模仿;而同时也表明他对表达的需求——他可能意识到大众文化产品背后联系的产业体系和资本,以及代表权力的媒介渠道,所以他通过几乎没有成本的模仿和同样几乎没有成本的互联网发布渠道来进行自我表达。而无论是如胡戈般出于批评,还是单纯地出于娱人娱己的愿望,他的行为已经完成了对大众文化产品之中资本和权力的消解。而当看客们乐于观看、传播、分享和命名“山寨文化”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完成了将大众文化产品指认为“精英文化”,至少是某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的过程,从而获得一种想象中的胜利。“山寨文化”正是其制造者和传播者通过命名行为来确认表达和言说的能力,进而确认某种他们需要的主体性。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罗兰·巴特的表述,这正是一种颠覆秩序的行为,不仅有表达,也有行动;然而所颠覆的,只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工业中的资本确立的某种语言秩序而已。
四、结语
“山寨文化”会不会越来越流行?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首先,前文已经提到,“山寨”的最终目的正是“受招安”,如果“超级女声”都可以因“本土化”而成为主流文化,那么讨论这个问题只会变成争论什么东西是“山寨的”,结论大约不会超出韩寒的那篇短文。其次,“山寨文化”不可能离开原文本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山寨”永远是一个与 “主流”(暂且这么命名)相对的表述,“山寨文化”内在的主流文化的视点,必然会让热衷“山寨文化”的网民在偏离之后回归,在狂欢之后清醒,他们所拥有的,只不是一个表达而已,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大众文化工业已经坚不可摧。然而重要的却恰恰正是这个表达,其具备的颠覆性已经告诉我们某种统一的话语开始解体,另一些话语开始浮现。由此有人称“山寨是中国新兴的公民社会”,这大概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黄集伟:《他的囧,你的槑,我们心中巨大的雷》,《南方周末》,2009年1月21日。
[2] 逆转录猴子的豆瓣日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http://www.douban.com/note/2605548/。
[3] 韩寒新浪博客:《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cbzk.html。
[4] 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5] 黄集伟:《他的囧,你的槑,我们心中巨大的雷》,《南方周末》,2009年1月21日。
[6] 胡续东豆瓣日记:《关于网络流行语,我十分打酱油地窃以为……》, http://www.douban.com/note/28715688/。
[7]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