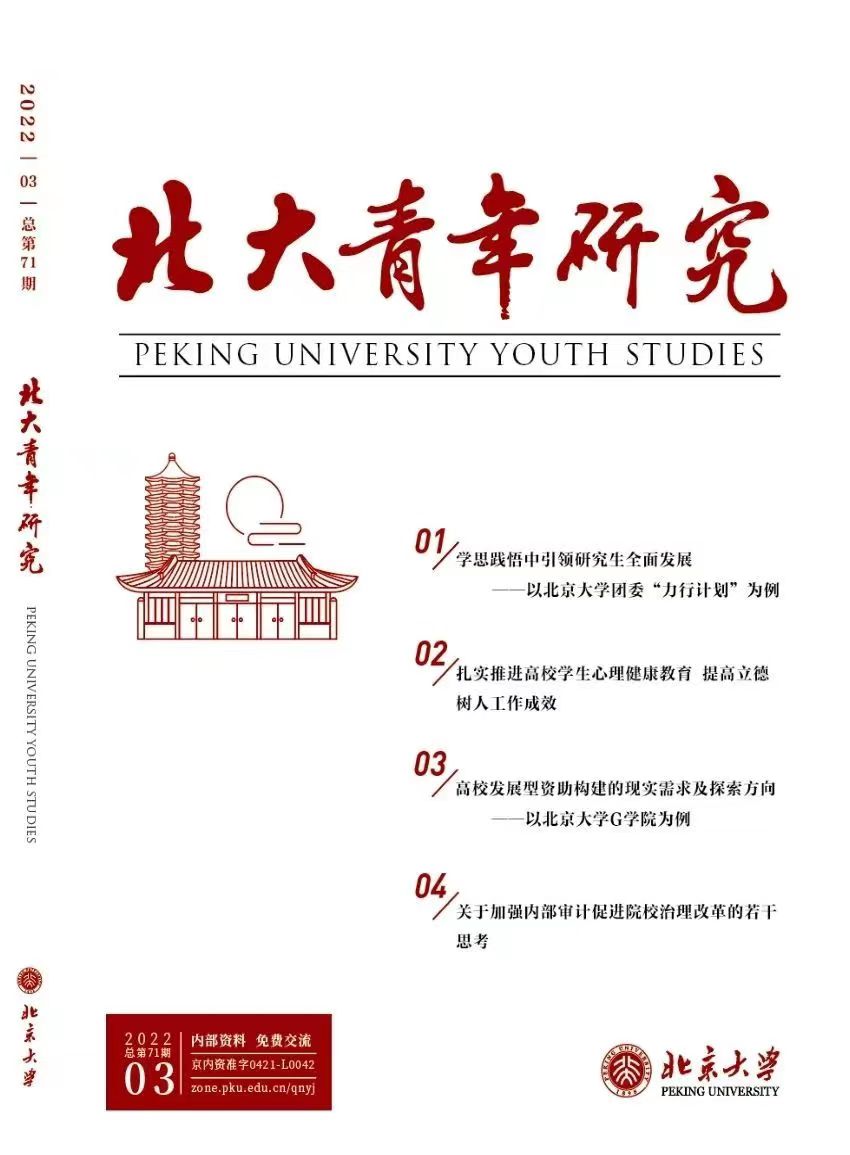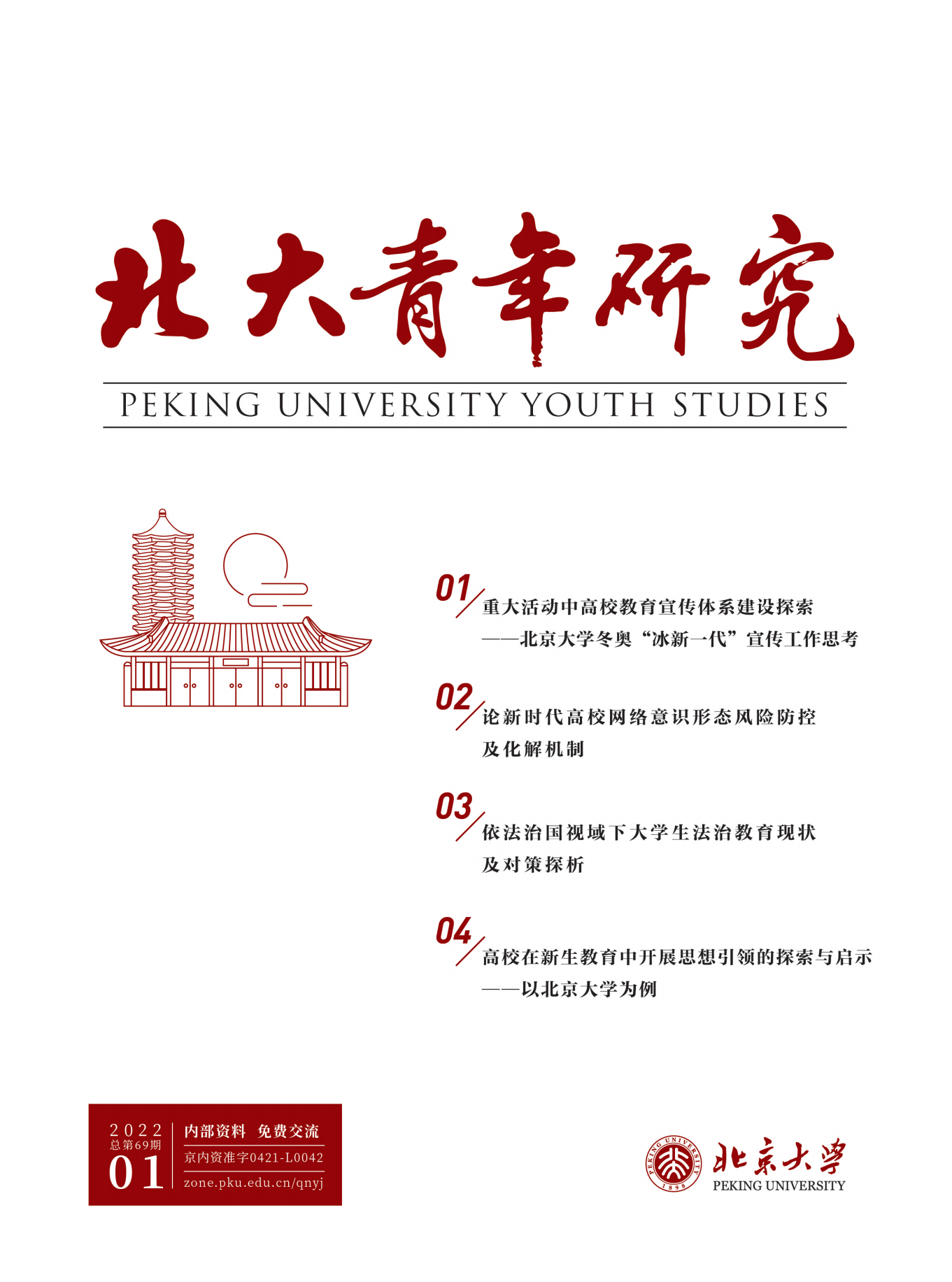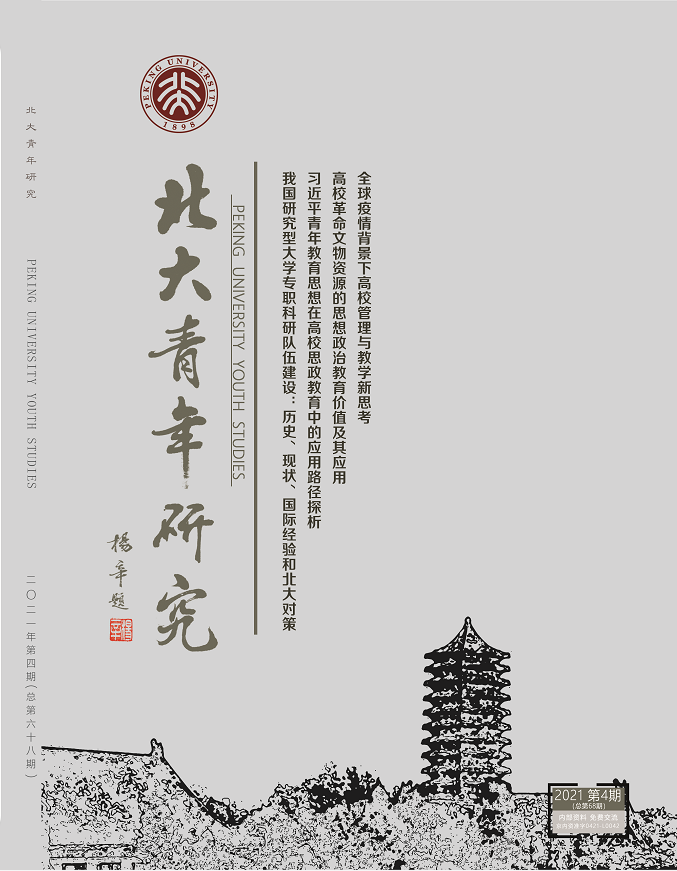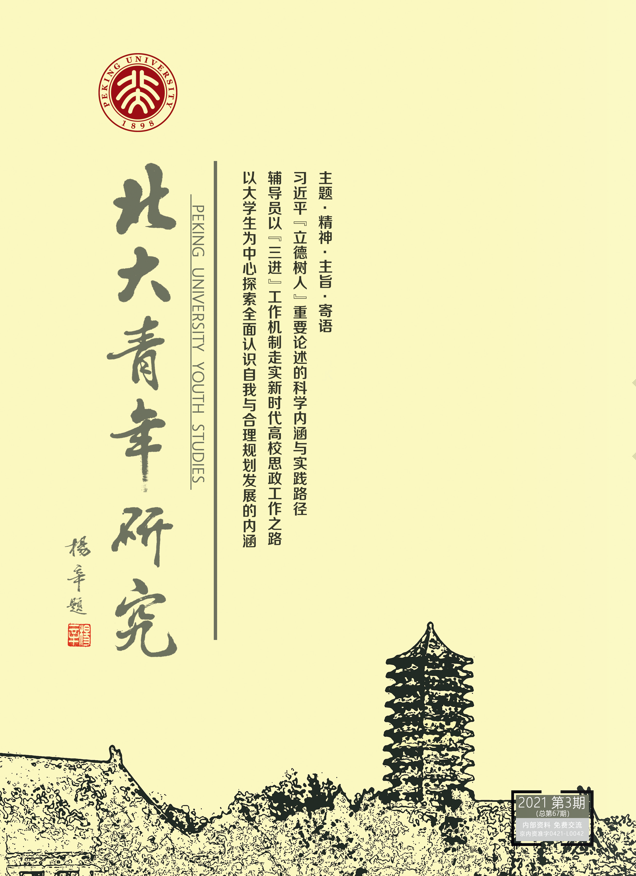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网络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从戈夫曼“拟剧论”视角出发透视当代大学生社交网络生活
1924年,斯坦尼拉夫斯基旅居美国期间出版了自传《我的艺术生活》,在其中他写道:“内部的自我修养在于锻炼内心技术,使演员能在自身唤起创作的自我感觉……外部的自我修养在于使形体器官准备好去体现角色,并精确地把角色的内心生活表达出来。”20年后,同样具有斯拉夫血统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通过他著名的“拟剧论”,引入了前台与后台、给予与流露等概念,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无意中呼应了斯氏的断言。
1982年,戈夫曼逝世。其时,比尔盖茨刚刚推出DOS操作系统,大洋彼岸的马化腾还在上小学。戈夫曼无缘得见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无法见证社交网络的大行其道,但戈夫曼和他所遗留的学术思考却一直处于社交网络研究的视野之内,被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学者们不断研究和发掘。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交网络为我们的自我呈现带来了哪些变化?本文尝试以当代大学生为研究主体,从戈夫曼和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出发,关注探讨自我呈现研究在互联网中经受的变迁与挑战。
一、表演还是陈列?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互动”(interaction)界定为“当若干个体彼此直接在场时,他们对相互行为的交互影响”[1],一组特定个体持续在场的所有互动可以被视为同一次互动,也就是“同一次的日常接触”,而一个个体在任何特定场合所表现出的行为可以算作一次“表演”。虽然戈夫曼也扩展了“表演”这一概念,使其不局限于面对面,也包含了他所谓的微弱联系,即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不一定发生直接的面对面交往。但“持续在场”这一要素对于互动和表演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互联网交往中,持续在场这一条件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满足的。表演者在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只是一段文字、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或其组合。观众只是将自己的注意力偶尔投射到一个对话框、一条朋友圈动态、一篇博客文章。即便是观看直播,能目不转睛地从主播开播看到下播的毕竟只是少数,何况主播也并不只是在应付一位观众。因此,如果要对戈夫曼的“表演”概念进行扩展的话,其实互联网中的交往更接近霍根所说的“陈列”(exhibition)[2]。
陈列相对于表演,其区别单从喻体上就可以看出端倪。首先,陈列的展品可以是割裂开来的,展品和展品之间可以没有任何连续性;而表演总是连续的。其次,陈列品可以被反复欣赏,而本轮表演结束后就结束了,即便是下一场演出,和本场毕竟不是相同的。最后,展品的解读空间和角度更加多元,毕竟展品无法自己进行“解说”;而老练的表演者往往可以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表演,甚至有意引导观众往自己希望的方向理解。
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就在于陈列所处的是“线索隐退的环境”(cue-reduced environment)[3],表演者和观众其实并没有真正处于同一时空,而是通过自己在社交平台留下的展品为媒介进行互动。以目前最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之一微信为例,表演者所发布的不同朋友圈信息,其中传达的情绪或内容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一旦发布,只要表演者不删除或刻意隐藏,就会一直留在网络空间中等待观众的解读。而观众在解读时并不会仔细考察表演者在发布这条信息时所处的具体情境,事实上,表演者自己很多时候也会忘记当时自己为什么要发这么一条信息。这就导致,某人多年前发布的一条信息,在某一时刻突然被人或有意或无意的发现,而其中刚好又包含了某些引起误会的内容(不论这内容是当时有意为之,还是因为当下语境改变产生了新的内涵),那么此人很可能会面临一场范围或大或小的舆论讨伐,不少新晋明星或“网红”就经历过这种事件。即便是最新发布的信息,也会因为“线索隐退”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一位大学生在她的朋友圈中写道“今天是祭日”,立刻就会引起她的周围同学或辅导员的恐慌,特别是,这位同学也许平时在生活中就表现得多愁善感,就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判断。等大家好不容易联系上这位同学,才得知,她所谓的“祭日”是“祭奠我死去的爱情”——去年今日,她遭遇了失恋,今天想起此事,发一条朋友圈以资纪念。
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有的表演者会及时清理或隐藏自己发布的信息。朋友圈“半年可见”“一个月可见”甚至“三天可见”就是例证。或者通过注册“小号”来隐藏自己,但其实效果有限,而且拥有多个“马甲”(小号的一种别称)这件事情本身,在部分观众看来就值得怀疑。因此,在网络上展示自我的最好策略,恐怕还是在“展品”和“布展”上下功夫。
二、强化给予与隐藏流露
上文提到,网民会通过刻意删除来试图隐藏自己,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就是通过有意识地雕琢自己发布的信息,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这里有必要引入戈夫曼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前台”(front stage)。前台即“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地使用的标准类型的表达装备”[4]。我们对前台的操纵,即“印象管理”,通过一些手段来塑造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塑造往往带有夸大成分,即突出自己的长处)。
现实生活中的印象管理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因为存在许多现实困难。这种困难可以用戈夫曼的另一对概念来解释,“给出”和“流露”。给出包括“各种词语符号或他们的代替物,个体用这种公认的和唯一的方式,来传达他与他人都知道的附于这些符号中的信息”;流露包括“范围广泛的行动,他人可视其为行动者的表征”[5]。简单来说,给出指的是自己有意向别人展示的信息,流露指的是自己无意间传达的信息。小动作、表情甚至眼神都可以被归为流露的范畴。在当面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把控自己流露了哪些信息,因此在现实中,人们难免遭遇印象管理中的失败。
而在社交网络中,网民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手段强化给出同时弱化流露[6]。文字可以精心编辑,甚至可以通过引经据典来彰显自己的博学;照片可以精修,五官上的瑕疵或身材的不完美在美图软件的加持下都不再是问题;甚至视频和音频现在也可以通过各种软件或硬件实现美化。
这种对自我形象更强的掌控,不仅意味着网民更容易产生“自带光环的幻觉”[7],而且意味着网民为了维持这种幻觉会不断强化以上两种倾向,最终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不断突出自己为观众所赞赏的特点,甚至走向极端的程度;二是为了持续获得观众的赞美,选择性地屏蔽观众。第一种情形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位在日常生活中还算彬彬有礼的同学,在社交网络发表了一些讽刺时政的内容,受到部分网友的鼓励,为了持续获得这些观众的认可,他的观点越来越极端。最初也许按照他的辩护,尚且是“抖机灵”,但后来,文字越来越不堪入目,简直是谩骂和侮辱了。这种变化其本人很可能是不自知的,在网友的吹捧和鼓动下,他逐渐变得越来越偏激,以至于影响到他与别人的现实交流,自己却依然沉浸在社交网络带给他的虚荣之中,幻想自己已经成为了“意见领袖”,其实不过是沦为了“网络暴民”。这说明,强化给予不仅会扩大精致理性的一面,也会促使狂暴冲动的一面滋生蔓延。现实是纷繁的,更是连续的,其复杂性就隐藏在每个人不经意间的流露中,但网络消弭了这些可能性,而只留下孤立破碎的片段,本质上还是对现实的扭曲。
三、后台与观众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必须放置在具体的边界中进行考量,即表演者和观众之间、不同表演群体之间都有着明确的边界。但社交网络中是否存在这种边界是一个问题。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引入戈夫曼的另一个关键概念:观众隔离。所谓观众隔离,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或一群人进行自我呈现时,并不希望另一个或一群人毫无预兆地闯入。这些不速之客可能会打破我们既定的表演剧本,让我们手足无措。例如夫妻的争吵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会希望在争吵的时候,另一位与他们熟识的朋友撞见这件事情。
尽管沉迷于社交网络的网民试图在网络上重构一个全新的自我,但现实和网络总是要彼此纠缠在一起。甚至,线上与线下的边界有时也不那么清晰。要想实现理想的表演,需要成功的观众隔离。成功的观众隔离至少需要有两个具体的前提:首先观众是可被识别的;其次观众是可被隔离的[8]。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前提往往都是可控的。不过,在社交媒体中,这两个前提都在遭受挑战。
关于第一个前提,在社交网络中,观众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不要说具体识别每一个观众的形象,即便是给自己的“粉丝”画一个群像也是非常困难的。面对观众退隐的环境,之前强化给予的努力也有可能遭遇失败。因为自己精心构建的完美形象很可能在部分观众那里一文不值。甚至,部分观众就是为了挑刺而不是欣赏才来关注表演者(这类观众一般被称为“黑粉”)。但在众多粉丝里,很难区分“真爱粉”与“黑粉” 。一旦表演者发生负面新闻或者发表不当言论(这种挫败被称为“翻车”),平时在舞台下方沉默的黑粉们会一拥而上,迫不及待“踩上一脚”或是抖出当事人更多可以用于攻诘的信息(即所谓“黑料”)。依然用上文的那位学生为例,平时他在朋友圈和微博发表一些不合适言论,既为他吸引来很多真爱粉,也招致了一大批黑粉,真爱粉的吹捧让他飘飘然,终于他由于在朋友圈发表过激不当言论遭遇了翻车。黑粉们蜂拥而上,不仅深挖他的既往朋友圈信息,将他微博上数个马甲的过往信息翻了个底朝天,并从中发现了更多黑料,甚至冲破社交平台,对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信息进行了“人肉”。
针对第二个前提,观众和表演者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这意味着观众隔离的难度越来越大。虽然社交网络提供了诸如分组可见、分组不可见等技术手段,但问题也显而易见。首先进行分组将会耗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以至于完全消磨掉从可见对象那里获得的正面效用,而且难免出错。例如,某位同学本来想屏蔽亲戚在同学中里发一些牢骚,结果操作失误(一般称为“手滑”)点了“仅亲戚可见”,招致父母的电话关心(或批评)。其次,组内的对象其实也在不断变化,而表演者不一定能及时调整分组。最终导致表演者在发布信息时采用的最好策略就是最小公分母原则(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9],隐藏自己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通俗来讲就是谁也不得罪。彻底切断流露的可能性,强化自己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一面。
四、结语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写到:“整个世界是个舞台,所有男男女女不外是演员,各有登场和退场,一生扮演着那么些角色。”同样的,社交网络也是一个舞台,只不过在这里,表演者需要费心思考的不是怎样登场亮相以吸引观众的驻足观看——社交网络上从不缺少观众和看客,而是如何体面的收场,结束自己的表演,继续现实生活。大学生们掌握了极强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运作自己的社交网络,但往往欠缺足够的审慎和节制来处理自己与粉丝、网络与现实的关系,所以有时会给自己招来许多本可以避免的麻烦。但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现实中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社交网络与其说是“双刃剑”,不如说是“试金石”;网络既是掩盖自身瑕疵的“遮羞布”,其实也是放大自己缺点的“显微镜”。现实中立不住的“人设”,在社交网络中也迟早会垮塌,只有自己立得住、把得牢、站得稳、行得正,才能经受住社交网络的检验。即便遭遇一些误会,一个在现实中正直的人也能有更大的解释余地。
总之,随着社交媒体的进一步普及,对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教育会越来越迫在眉睫,而这需要政府、学校、互联网公司乃至家庭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王 恒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讲师
刘东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团委书记 助教
参考文献:
[1][4][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22,2.
[2][9]Hogan, 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6), 377-386.
[3]Walther, J. B. (199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1), 3-43.
[6][7][8]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 2018(1)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