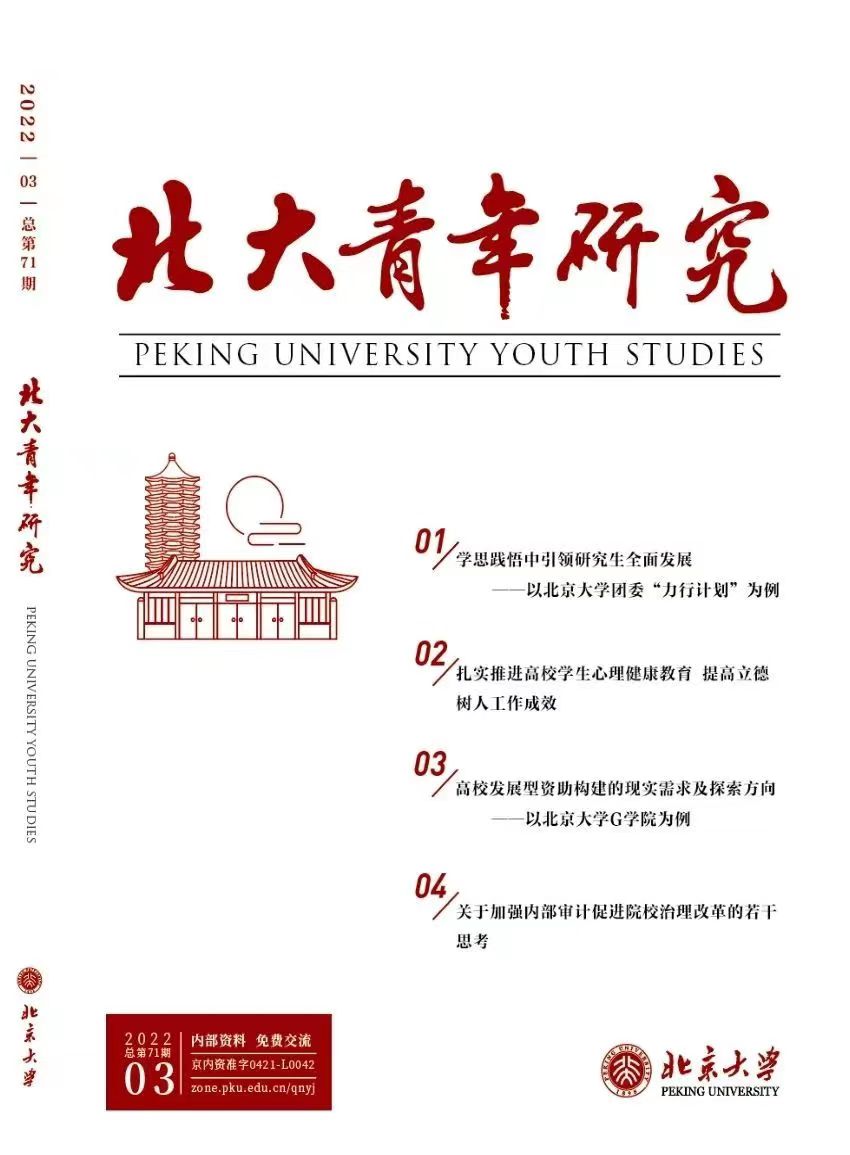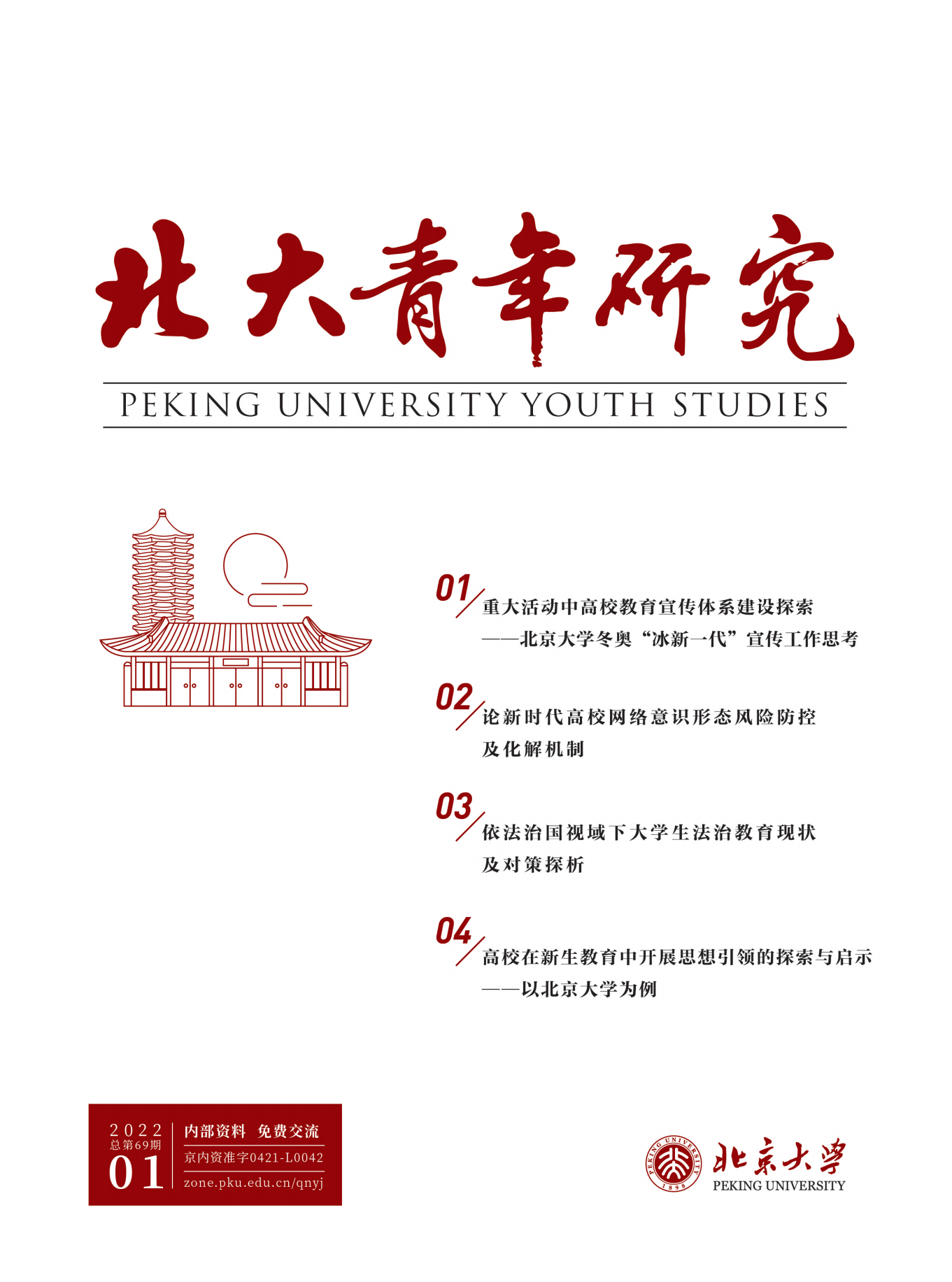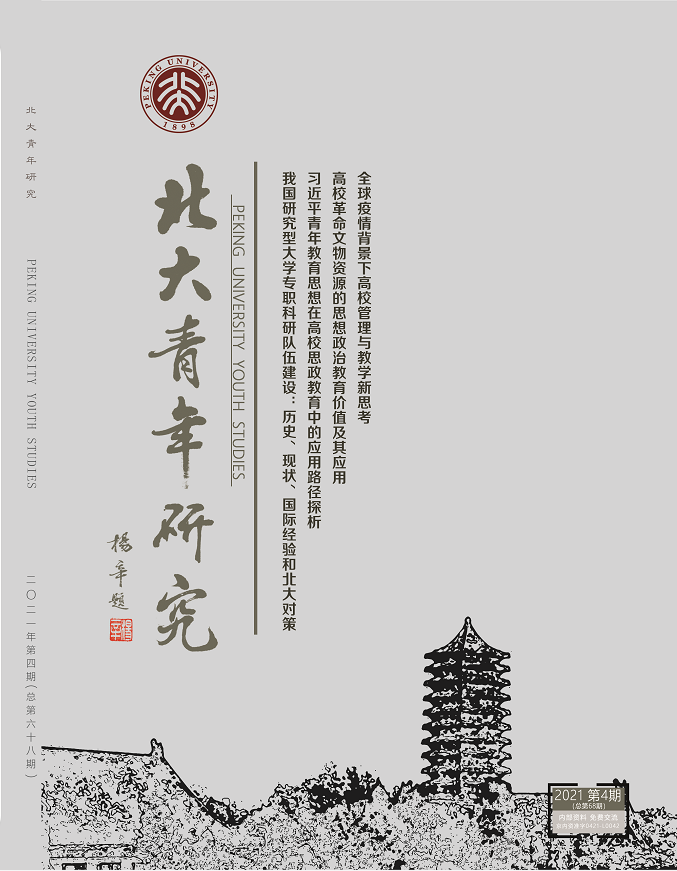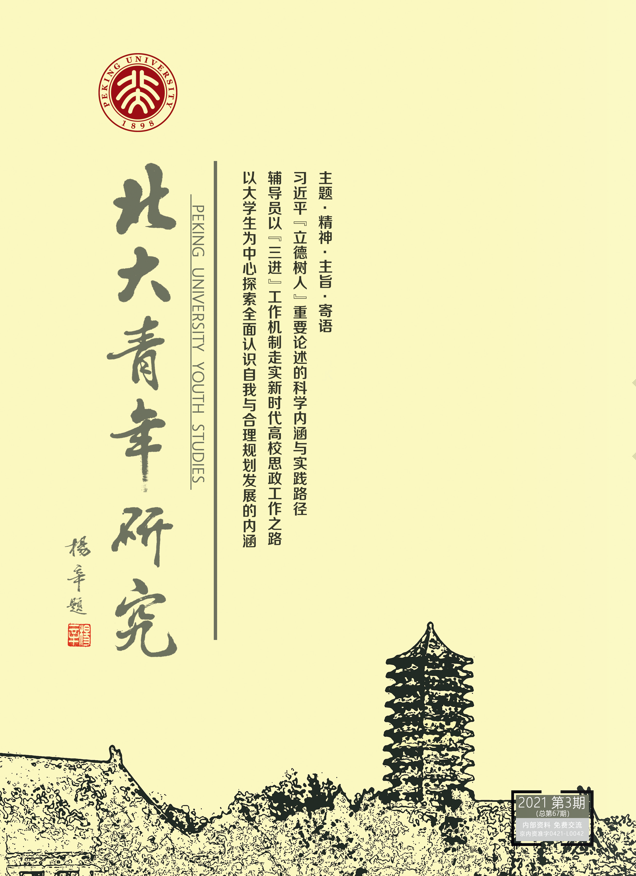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学习打卡”对大学生群体自主学习的影响——以北京大学在校生为例
摘要:“学习打卡”是打卡主体为实现自我监督,主动对其先前完成的某项学习内容进行记录的行为。作为新的学习场景下自我监控技术的新形态,“学习打卡”可以弥补人类注意、记忆等认知方面限制,一方面通过影响具有选择性且稀缺的注意力资源的配置,促进打卡者主动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检视和反思;另一方面,打卡记录作为一种“人工记忆”,可以使得学习活动具象化、可视化且可追溯,使打卡者了解自己和他人已完成学习活动的基本情况,并据此判断已完成的学习活动是否符合评价标准的依据。
关键词:学习打卡;自主学习;自我监控
一、引入
“打卡”一词起源于职场,最初是一种考勤方式,指员工将考勤记录卡插入磁卡机,用以记录上下班时间[1]。在长期实践中,伴随打卡工具和方式不断丰富,“打卡”一词衍生出新的语义和用法,从考勤术语变成一般用语,“入侵”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发展出支付方式、记录方式、习惯方式、参与方式、游览、宣传等多重含义[2]。其中,学习场景是“打卡”一词使用语境扩展的“主战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发地进行英语单词打卡、阅读打卡等“学习打卡”,各高校基层院系组织学生活动时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打卡记录一度在社交软件中刷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大学在校生为例,探究“学习打卡”如何影响大学生群体的自主学习。从理论意义上看,本文运用自主学习理论解读“学习打卡”现象,对新的学习场景下自主学习中的自我监控等内容进行再思考,有利于丰富理论内涵。从现实意义上看,一方面,本文所关注的“学习打卡”现象,是高校制度化学习以及互联网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行为,在形式和动力机制等方面不同于参与学校学习活动,有利于全面理解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态。另一方面,如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可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始终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传统意义上学校面对面的教学活动难以进行,高校全面组织实施线上教学活动,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探究“学习打卡”对大学生群体自主学习的影响机制,可以为改善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问题提供应对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文以自主学习能力强①、“学习打卡”经历丰富②的北京大学在校生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总的抽样设计为目的性抽样,受访者均为“学习打卡”经历丰富的个体,从而为研究问题提供密集、丰富的信息。在具体抽样策略上,考虑到疫情期间难以进行面对面访谈,而陌生人往往不愿意接受视频通话,不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和非言语信息的获取。因此,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受访者均为相识的同学和朋友。
本研究共对七名受访者进行了访谈,下表为各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和特征:
表1:受访者基本情况与特征
|
受访者 |
年级 |
院系 |
性别 |
“学习打卡”类型 |
|
H同学 |
大四 |
外国语学院 |
女 |
英语外刊精读 |
|
P同学 |
研一 |
法学院 |
女 |
英语单词、口语、听力 |
|
Y同学 |
大一 |
药学院 |
女 |
英语单词 |
|
X同学 |
大一 |
药学院 |
女 |
英语单词 |
|
L同学 |
大一 |
生命科学学院 |
男 |
英语单词、日语单词 |
|
W同学 |
研一 |
教育学院 |
女 |
每天学习时长 |
|
Z同学 |
研二 |
政府管理学院 |
女 |
每天学习内容 |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为访谈。以上七名受访者均接受了半结构化的一对一访谈,每次访谈约为四十分钟。数据收集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因此所有的数据收集均通过互联网进行。除了与Z同学进行微信语音访谈外,其余六名同学均为微信视频访谈。受访者接受访谈的地点为家中,处于舒适的环境,身心状态比较放松。对话偶尔会受到网络状况的影响存在延迟,但是,总的来说访谈过程比较顺畅,交流比较充分。除了在访谈过程中作记录外,还在获得受访者同意后,对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第一时间整理成文字稿,尽量减少信息的损耗和失真。
本研究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阶段交替进行。在前四个访谈结束后,开始数据分析工作,并以数据分析初步结果作为后续访谈工作的方向指引。数据分析的主要方法为编码和撰写备忘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属分析,建立资料之间的联系。
三、“学习打卡”与自主学习
(一)与自主学习伴生的“学习打卡”
自主学习一般指个体自觉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或能力[3]。在与全部七名受访者就“学习打卡”经历进行交流后发现,受访者的学习过程表现出自主学习的若干特征:
就学习动机而言,受访者的学习是自我驱动的。L同学这样描述自己开始英语单词学习的情境:“我上个学期报了一个英语词汇学的课程,是个B类课,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哇,我好差啊,怎么什么单词都不会’,然后想背(单词)。”这里L的学习始于掌握知识、增长词汇量的内在目标,并非源于外部要求。换言之,是“我要学”而非“要我学”。
就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等具体学习方面而言,受访者是自主地做出选择和控制的。P同学谈到自己最近一次开始“学习打卡”时表示:“首先是有一个动力,是觉得我应该学习英语了;学英语能干啥呢,那就背单词、练听力、练口语。有了目标之后就是选软件,扇贝单词和每日英语听力这两个软件是(英语学习中)比较常用的。单词每天背250个,背的慢的话可能要90分钟到120分钟;然后听力的话,比较弹性,控制在25分钟之内。每个上午基本上都用来学英语。”这里P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内容(单词、听力、口语)是自己选择的;学习策略(使用手机应用软件)是自己确定的;学习时长是自我计划、自我管理的。
就学习的外部环境而言,受访者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于学习的物质和社会性条件。L同学谈到自己“学习打卡”是为了寻求外界“自愿的监督者”,在他“一个人很难调整的时候(比如沉迷游戏无法自拔的时候)”,能够有人“敲一榔头”,提醒他去学习:“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大概让别人知道我在运营这样一个……我在干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如果我咕了很长时间的话,不说别人,就是我的父母也会问‘诶,你最近怎么不打卡了’”。尽管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带有一定强制色彩,但是这种关系是L主动选择的结果;究其本质而言,L是在主动地向外界寻求帮助、调整学习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上文所介绍的L和P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七名受访者学习过程的典型代表和缩影。为什么有过“学习打卡”经历的受访者的学习过程普遍具有自主学习特征?“学习打卡”与自主学习之间是什么关系?下文将结合访谈内容从自主学习的自我监控等环节出发,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学习打卡”与自我监控
自20世纪70年代“自我监控”概念提出后,学者围绕自我监控与自主学习展开了系列研究,自我监控被视为自主学习的重要环节和能力。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操作主义学派将自主学习分为自我监控、自我指导和自我强化三个子过程,自我监控即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所进行的一种观察、审视和评价[4],对学习活动过程的直接叙述、对学习行为的记录等均为常见的自我监控行为[5]。以齐默尔曼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学派指出学生在元认知、动机和行为等三个方面的积极参与是认定自主学习的标准[6],元认知即对认知的认知,包括学生的自我监控活动。国内学者董奇和周勇在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的研究中指出,对学习过程的监察、评价和反馈及在此基础上对学习活动的调节、修正和控制,是学生主动、独立、自觉地从事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的表现,是自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7]。
在受访者的学习过程中,“学习打卡”在自主学习的自我监控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打卡”可以引导打卡者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已完成的学习内容上,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总结。W同学谈到:“看到之前有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就会想说其实我也是可以学习这么长时间的,只是我最近在干嘛呢?(笑)有一点点记录自己过去努力的痕迹,然后对现下经常起到一个提点的作用吧。”W经历了每日学习时间由长变短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学习打卡”的记录中。当W查看既往打卡记录时,引发了她对于最近一段时间学习状态的反思,并根据反思的结论对当下的学习活动及时进行调整,也就是她所谓“起到提点的作用”。
学习的自我监控根据范围和时间可以分成宏观和微观两种类型[8],W对自己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学习活动的观察、审视和评价属于宏观的学习自我监控,而Z同学的“学习打卡”经历则展现了较短周期内的微观的学习自我监控。Z谈到:“这个记录……我用来看一下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有没有抓紧时间或者浪费了多少时间,是对今天的一个反思。”Z在记录自己每日学习内容及对应时长的时候,实际上完成了对当天的学习活动、特别是时间管理情况的审视和评价。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9]。受生理条件限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和范围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同时关注到所有的事情,换言之,注意具有选择性。与高中阶段以“高考”为指挥棒、“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同,大学生活除了学校的学习活动外,可供学生自主安排的业余时间很多[10],大学生群体面临着学习、社团、学生工作、社交、娱乐等共同构建的多任务环境,这加剧了对本就稀缺的注意力资源的争夺。正如Z所描述,“每天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把你的时间搞得支离破碎。”因此,如何合理分配注意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心理学领域的既有研究显示,注意力分配一方面受到外界刺激的诱发,另一方面受到大脑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影响。[11]具体到打卡场景之中,“学习打卡”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注意力的配置:其一,打卡记录作为一种外部刺激物,当打卡者看到自己的学习记录时,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已完成的学习活动当中,上文中W看到每日学习时间的记录后对学习状态的反思,是这一影响注意力配置方式的实例。其二,打卡者将在一定时间周期内完成“学习打卡”作为一项任务,在这一任务驱动下,在打卡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至自己所完成的学习活动当中,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检视和反思,上文中Z每天记录学习内容及对应时长即属于这种影响注意力配置的情形。
第二,在学习评价的问题上,W同学谈到:“我看我导的那种很难很难的材料,如果我看了两个小时,我看懂了一点点,我理解了一点点,我会觉得我今天的学习还蛮有效的,我也不会很在乎那个时间;但是如果是看比较简单的东西,或者说背单词,我会比较在意那个时间,就是我今天学了多长时间,我背了多少个单词,我会比较在意那个数量。”这里W依据难易程度将学习内容分为“很难很难的知识”和“简单的”“纯靠背或者是个人就能理解的东西”。在此基础上,W指出她对有效学习评价的标准:对于前一类很难的知识,能够“理解一点点”就是“蛮有效”的学习;对于后一类相对容易的知识,她更看重数量,比如“学了多长时间”“背了多少个单词”。
以数量作为学习评价标准在受访者中并非个例,L同学谈到:“我大概有个标准就是,那两个语言(英语、日语)……如果这两个加起来,我只漏了5天以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月干的还不错这样。”这里L同学以一个月内的语言学习天数作为学习评价的标准;Y同学在评价共同学习的同学时,也突出了数量的概念:“那里面有几个大佬特别强,他们每天能背八百多个单词。”此时,“学习打卡”使得学习活动具象化、可视化,可能影响学习评价具体标准的确定;“学习打卡”使得学习活动可回溯,很多情况下打卡记录成为打卡者评价自己学习过程的依据。
首先,在学习评价具体标准的确立问题上,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显示,足够好和不够好的分界线是不稳定的,个体会根据自己的过往或者他人的“业绩”对目标和标准进行调整[12]。比如,X同学曾谈到“别人背1000(单词),我背100……如果我想在数量上追求跟他……那样的话,我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这里别人背单词的数量,使X对自己之前确立的100个单词的有效学习标准产生了动摇。因此,很多时候有效学习标准的确立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这要求学习者知晓自己过往或者他人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学习打卡”将学习过程这一抽象的、无形的脑力活动,转化为可供自己和他人查看的、具体的文字记录,使得学习活动具象化、可视化,而且查阅不受时间限制,使得个体很容易了解自己过往的和他人的表现并进行比较、调整,从而确立合理的学习评价具体标准。
其次,受生理结构限制,个体储存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单凭自然记忆[13],很难准确记住学习时长、天数和完成的学习任务数量,这会影响个体判断一段时间内学习活动是否符合学习评价标准,上文中L同学可能会记不清一个月内自己进行了多少天语言学习。此时,“学习打卡”通过记录保存的“人为记忆”,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并作为对学习活动进行评价的依据,比如上文中W同学会根据每周打卡记录中的数据统计,判断自己近期的学习是否有效。
四、发现与启示
本研究关注大学生群体自发进行“学习打卡”的文化现象。所谓“学习打卡”,是指打卡者为实现自我监督,在完成某项学习内容后主动进行记录的行为。其中,记录是其核心的外在行为表现;展示、分享行为在大部分“学习打卡”中出现,但并非其必备条件。在与全部七名受访者就“学习打卡”经历交流后,发现受访者的学习过程普遍地表现出自主学习的若干特征,进一步聚焦至“学习打卡”与自主学习的关系,最终确定的研究问题是:“学习打卡”对大学生群体自主学习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学习打卡”可以弥补人类注意、记忆等认知方面限制,主要在自主学习的自我监控环节发挥作用,推动打卡者对学习过程的监察、评价和反馈,以此改善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效果和自主学习能力。第一,“学习打卡”可以影响具有选择性且稀缺的注意力资源的配置。就被动注意而言,打卡记录作为一种外部刺激物,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将注意力引导至先前完成的学习活动;就主动注意而言,打卡者将在一定时间周期内完成“学习打卡”作为一项任务,并在任务驱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配置注意力,促进打卡者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检视和反思。第二,“学习打卡”、特别是打卡记录是一种“人工记忆”,使得学习活动具象化、可视化且可追溯,使打卡者了解自己和他人已完成学习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比较中调整、确定学习评价的具体标准,并作为判断已完成的学习活动是否符合评价标准的依据。
自我记录是自我监控理论下训练自主学习能力的常见方法,学生主动地对学习过程或者结果进行记录,有助于优化自我观察,捕捉学习表现相关信息,帮助学生将自己的表现与标准进行比较[14]。对于将打卡记录自己保存的打卡者而言,“学习打卡”实际上就是自觉地运用自我记录的学习策略,改善自己的学习效果;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选择将打卡记录在一定范围内分享、展示,此时“学习打卡”的性质变得复杂:单从学习的视角出发,这不仅包含自我记录的学习策略,还是一种自我发起的社会学习形式——打卡记录使得学习活动可视化,个体可以看到他人的学习情况,自己的学习情况也展现在更多人的面前,从而在同伴、老师处获得社会支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学习打卡”是“数据化的自我运动” [15]的组成部分,打卡者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量化,分析相关数据并作出调整,以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
“学习打卡”诞生至今,曾经盛极一时、在社交媒体中出现“刷屏式打卡”;也承受了许多骂名,一度被批判为“一场全民表演”[16]。诚然,现实生活中存在流于形式的虚假打卡现象,但也有许多人通过“学习打卡”留下“努力的痕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助力。本研究通过倾听七名受访者的打卡故事,尝试触碰层层包装下“学习打卡”的实质——至少是实质的一角,将其总结为新的学习场景下自我监控技术的新形态,可供教育领域从业者参考改善学生的自主学习问题,并完成对“学习打卡”现象的正名。
作者简介:赵雪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国内学者对自主学习的实证研究显示,“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著高于一般院校学生,这种差异源于本科招生生源以及高校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引导和培养。
② 北京大学许多院系曾组织开展“学习打卡”活动,树洞等校内论坛常有人分享学习打卡记录。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订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678.
[2]孙宝新.“打卡”新义新用[J].语文建设,2019(09):71-72.
[3]庞维国.自主学习的测评方法[J].心理科学,2003(05):882-884.
[4][6]庞维国.论学生的自主学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02):78-83.
[5]周勇.国外自我监控学习理论综述[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3(03):49-53.
[7][8]董奇,周勇.论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8-14.
[9](美)詹姆斯·G.马奇(James G. March).决策是如何产生的[M]. 王元歌,章爱民.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7+17-20.
[10]黄兆信,李远煦.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研究——从高中与大学衔接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0(05):83-85.
[11][12]练宏.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5,30(04):215-241+246,16-17.
[13](美)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管理行为[M].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88.
[14]Athanasios Kolovelonis,Marios Goudas,Irini Dermitzaki.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oals and self-recording on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 motor skill in a physical education setting[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10,21(3).
[15]梁维科,石勇.解读青年“数据化的自我”风潮——从“数据化的自我”到“数据记录狂”[J].中国青年研究,2014(01):95-98+103.
[16]闫明.“全民表演”:社交软件中“打卡学习”行为动机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9,5(13):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