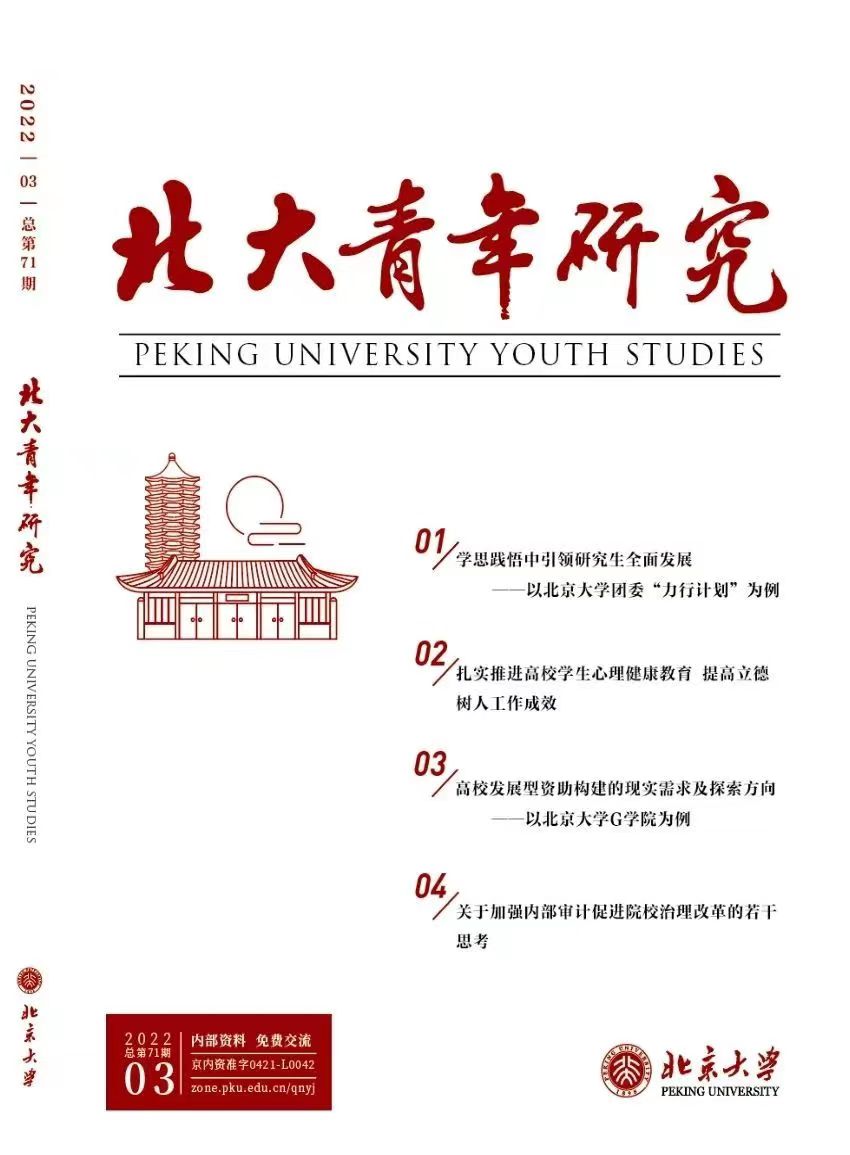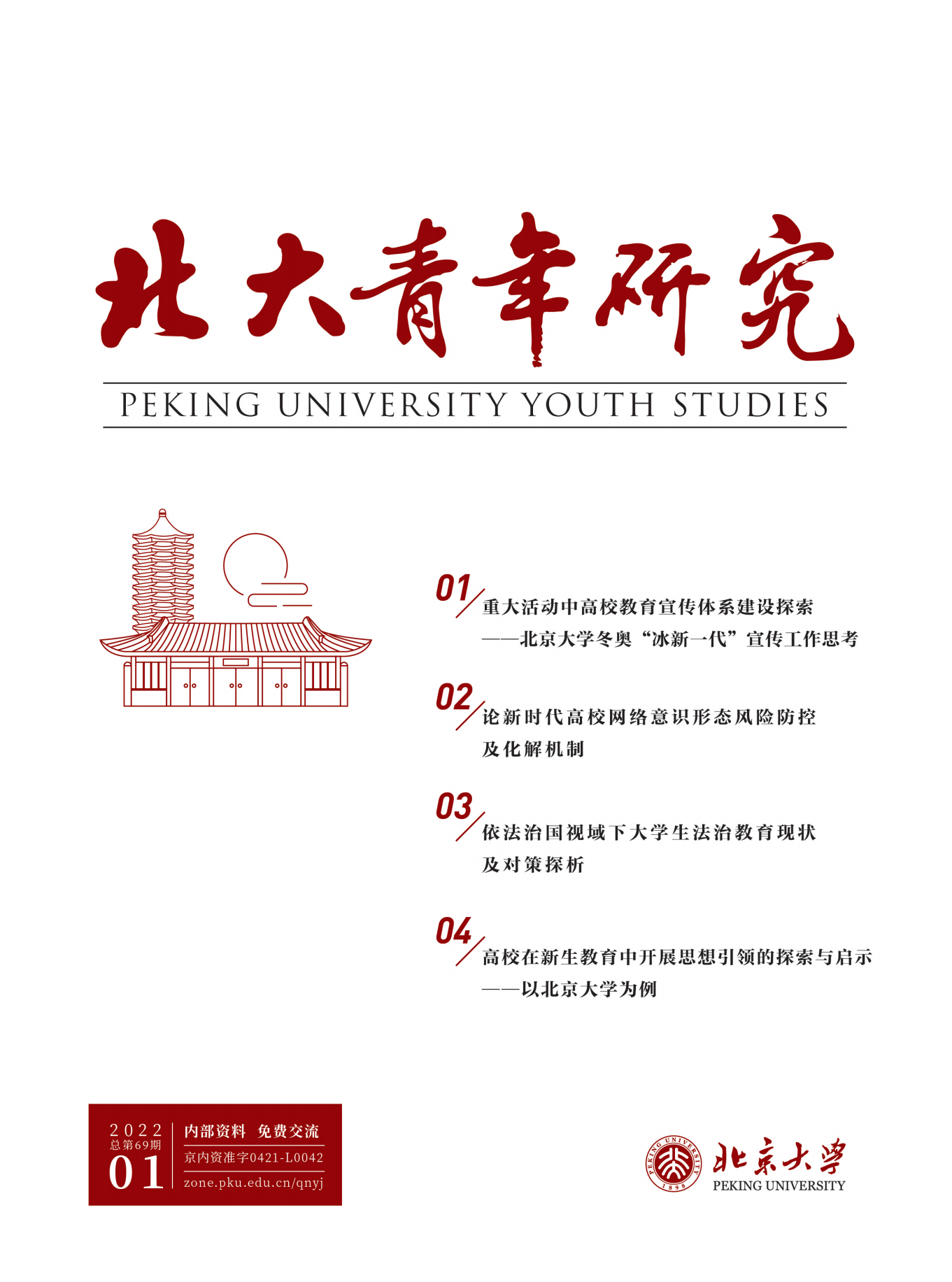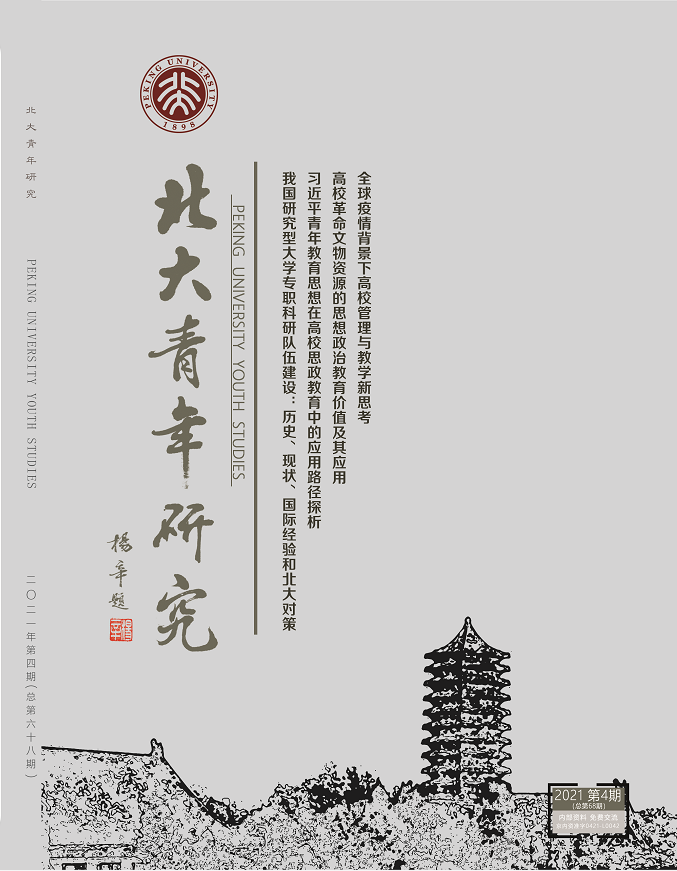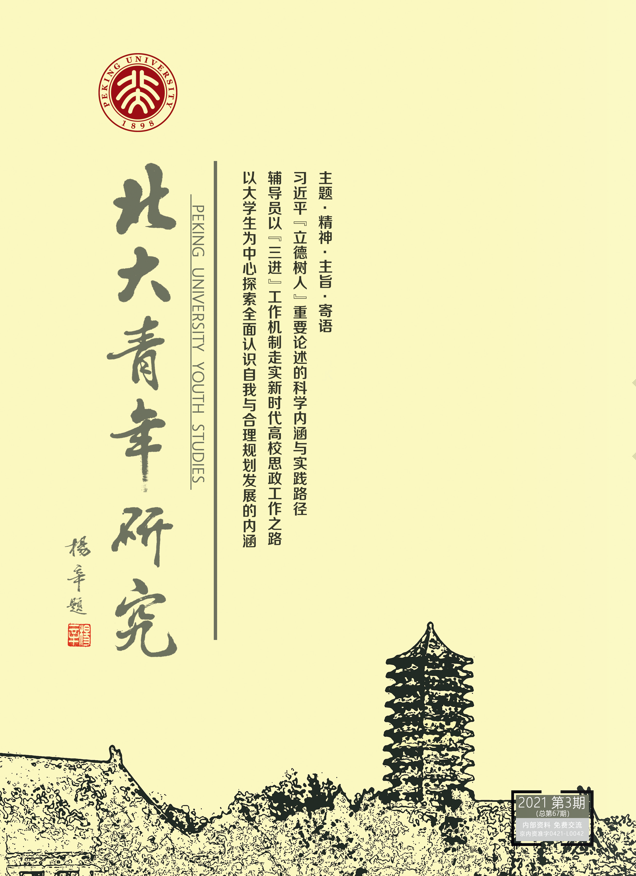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
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社长)
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如何实施办学方式的多样化和提高教学质量 ——读王义遒著《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下)
在上篇中,结合王义遒教授著作《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以下简称《高教》),我具体谈了“何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学精神”。下篇我想就作者的直接阐述,着重谈谈“为何出现办学模式的趋同化倾向”和“当前大学教育教学质量问题的关键何在”这两个方面的共识。
一、为何出现办学模式的趋同化倾向?
这是《高教》全书讨论的重点。作者用大量篇幅反复强调办学必须实施多样性,反对当前许多学校漠视差别,失去特色的趋同化倾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40%,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有重大意义。但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稳定有序地进一步扩大教育大众化,乃至趋近普及化,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可循。在这种形势下,过分讲究“一律”的趋同化倾向,却成了当前继续推进大众化、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大障碍。作者认为,克服“趋同化”弊端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实施多样化。多样化应当是大众化的前提。高等教育多种形式地展开,乃是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一)实施多样化,反对趋同性
所谓多样化,既包括教育机构的类型、层次、办学主体、服务面向等方面的差别,又包含因满足社会不同需求和个人主体差异所形成的学科类型、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师资结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作者概括为“机构多样化”和“管理多样化”(或“纵向多样化”和“横向多样化”)。关于前者,我国当前一般将大学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本科大学(学院)型、专科学院型等几个层次。
多样性胜过单一性的优越性十分明显。比如,学校类型、学科、专业的多样划分,可给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也便于学校依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确定自己的定位和目标,从而办出自身的特色。又如办学主体的多样性,由过去单纯的“官办”逐渐过渡到“官办”与“民办”并举,或“官民共办”,这就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开创更为广阔的途径。还可多渠道地筹措经费,扩充教育经费的来源。再如在管理制度上,蔡元培曾吸取西方办学经验,提出“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原则,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更为频繁而复杂。除了学术和教学上的重大原则问题,主要应由一定的教授组织讨论、决定外,许多经济、行政事务问题若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仅容易分散教授们治学、从教的精力,而且往往比较难于解决或处理不当。这需要一个富有管理经验和办事能力的集体班子来治理,也便于积累经验,保持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因此,可结合我国实际,比较灵活多样地安排管理制度。
作者指出,提倡多样化,并不否认高等教育有统一的办学规律,但这种统一性正是体现在多样性之中。不管哪种类型、哪种性质的学校,都需要提高,追求卓越。但这是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毕业生达到优质水平,积极地为国家或地方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而彰显自己的特色。这并不是说,所有地方本科大学都要争取设置硕士点、博士点,把“提高”理解为“上层次”“上档次”。在“博”与“专”的关系上,当前有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大学只是培养“通才”而不是培养“专才”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当今时代,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人,是不会有的,也是无用的。为了培养各种类型、层次的专门人才,通识教育对各个专业的学生都是必要的。通识教育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实际上是使学生学到怎么正确做人和正确做事的基本知识、态度和能力。通识教育也是为培养杰出人才和随后就业的多样选择准备条件,因此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可对立和偏废,二者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但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时间比例安排,不同类型的学校理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当前有些学校时兴培养“通才”,漫无边际地开些杂七杂八的课程,占去不少专业教育的时间,对于专业训练应有的实践与实习也往往置之不顾,这显然不利于人才的切实培养。
当前一些学校不顾社会需要和本校实际条件,大都盲目追求高层次、高档次,竭力向研究型、综合性大学靠拢。在攀高、升级心态的驱动下,千方百计争上硕士点、博士点,争当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乃至院士。为了争当“重点”,争设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而走门路、跑关系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高等学校的声誉。有的学校不求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单靠几个学校的简单合并,就以综合性、研究型相标榜,由“xx学院”晋升为“xx大学”,由专科学校晋升为“xx学院”的,比比皆是。这种盲目升级与趋同倾向,使得许多学校面目雷同,具体的定位和方向不明,使一些学校的原有专长逐渐淡去,使原来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骤然消失,而且容易导致学校之间的无谓竞争,使某些特殊而珍贵的教育资源被滥用、闲置和浪费。这会使高等教育逐步脱离社会的实际需要,使人才供需关系失调,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出现“无业可就与有业不就”同时并存的状况。还有人如此描述大学校园内一景:“大师已不见,技师也难找,倒有一群群身着方帽黑服的人满园跑。”
造成这种趋同化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政策措施的失当、办学定位不明,等等。但作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固守某种大学理念。其实,不论西方与国内,大学理念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二)认识大学理念的演变,加深理解多样化的必要性
所谓大学理念,是关于大学的性质、宗旨和怎样办大学的原则思考。作者指出:“是对一个理想大学的追求。”[1]
西方最早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治理大学的一般原则、方针都可看作经典的大学理念。大学当年从教会分离出来时,是一个研究和传授知识、产生知识的群众性的独立实体。知识在大学里有核心地位。世界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1088年。曾提出口号:大学即大家来学、来讨论的地方。可见按当时理念,大学是学者的一个共同体,一个传授和产生知识的共同体。到13、14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当时的经典大学理念集中反映在纽曼(Newman)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其基本理念是:大学是传授知识之地。追求知识,即追求真理,便是大学的目的。这种理念后来又有所发展。德国的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提出新的思想:1.教授自由;2.学术自由;3.教学与研究统一。这成为近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德国从14世纪至18世纪,成立了很多大学,逐渐形成了四大观念:1.修身,使人具备较高的文化、道德修养;2.科学,目的在追求真理;3.自由,学术自由,教授治校;4.寂寞,耐得住冷漠、辛苦,如我们所说,“坐得住十年冷板凳”“十年磨一剑”。
我国建立现代大学以来,蔡元培所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梅贻琦所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等,都来源于西欧的以上理念,他们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与“术”相区别。这种把大学看作脱离世俗功利、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实际是把大学看作“象牙之塔”式的圣洁的殿堂,是进行精英教育、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地方。当时他们主要是就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言的。
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理念也在发生较大的演变。美国真正的大学建成于19世纪。美国各州发展经济需要人才,办起各种大学,大学的功能也就随之扩展。除通过教学与科研培养人才外,还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服务。一大批政治家、经济家、外交家,多半来自大学。哈佛大学便为美国培养出八位总统。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雷达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兹实验室对美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大学摆脱了“学”与“术”相分离的经典理念模式,使科学与技术在大学里相结合,显示出美国大学的实力与优势。美国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技术推动,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不同类型、层次、特色的学校,使美国高等教育在保持精英教育的同时,首先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作者认为,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化阶段,体现了政治民主化和高等教育平等化的要求。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脱离市场,而是需要适应市场的要求。这就必然使大学的理念和办学模式发生变化。大学多了,经费短缺,不能单靠政府资助。必须开辟经费来源的多种途径,办学也必须讲究效益。在管理制度和模式上,不能一味强调“教授治校”,必须吸取有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的人,共同实行民主管理,可能带有某种企业管理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固守大学的经典理念,而应看到时代和历史的变化,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实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切实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当然,经典的大学理念的某些核心部分,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仍然是合理的。蔡元培、梅贻琦的基本思想并未过时。我们的民族需要大批社会精英,需要培养我们民族自己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笔者读《高教》后的一点重要认识和体会。
二、当前大学教育教学质量问题的关键何在?
这是当前人们极为关注、引起热议的问题。
所谓质量,作者认为,即事物的质的规定的量度。但教育质量的评估,不能单纯依据某些量化指标,而要由教育的目的、功用与受惠者的要求结合起来评估(学生是教育的直接受惠者,社会则是间接受惠者)。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般地说,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特殊地说,还有各级各类学校的具体培养目标。后者又可细分不同层次,并且比较容易实际操作。总的看来,教育教学的质量标准是相对的,具有多维度与多样性,也是与时俱进的,这当然增加了衡量与比较的难度。我国自进入21世纪高校普遍扩招以来,社会各界出现“扩招以后教学质量大滑坡”“量的扩展以质的降低为代价”等说法,提出种种质疑。作者对此持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
教学质量的保证与提高,关键在教师队伍的素养。作者在任北大教务长时,曾与当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朱德熙(著名语言学家)谈及教学方法问题,朱德熙说:“从来没听说大学还要抓教学方法的,教师有学问,就能教好课。”[2]朱校长谈到,教师搞好教学的“决窍”有二:一是教师要有学问;二是多从学生的角度着想。作者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质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作者以中国科技大学的三位数学大师(号称“三龙”)讲数学基础课为例:华罗庚,从学生身边事物引出数学问题;关肇直,高屋建瓴,富于哲理地分析数学问题;吴文俊,条理清晰,一气呵成地阐述数学问题。由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教无定法,”却“有道可循”。教学的高质量,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门艺术。教师只有对所教学科的内容下过功夫,十分熟悉,确有见解,并且关爱学生,尽力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才能不断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作者特别强调打好基础。基础是大厦的根底,“基础不牢,大厦难保”。本科生阶段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中心。我国大学本科的多数专业课程的体系,大致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建立的,往后虽有所变动,而基本构架比较稳定。但这种体系后来受到两次大的冲击:一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基本放弃了基础课程的稳步建设。1961年,教育部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过《高等教育六十条》,提出要“切实加强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教学”“切实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3]。这便是后来“加强基础”的源头。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大潮的涌动,人们纷纷下海经商,急功近利,从社会到学校,再次出现“读书无用论”的喧嚷。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高校,纷纷提出“强化基础”“夯实基础”“加强基础”的方针与口号。强调“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这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为过。
在本科阶段,一定要把基础打好。作者认为,我们的质量观,首先是基础质量观。它要求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品德的协调发展,获得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为国民素质的改善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根据学校的服务面向和结构定位,给学生以某种优势和特长的培养与训练,使之得到深造的机会与条件。这就要求在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上,需要一定的广度,使学生视野比较广阔,能高瞻远瞩。作者提到北大地质系,历史上出过4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系主任李四光让学生去听数学系的数学课、物理系的物理课,还可跟化学系、生物系的学生去做实验。这正体现蔡元培的沟通文理的理念。理科学生应当学些人文学科的知识,文科学生则应当学些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也正是当今大学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的某种要求。学校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为学生打好基础。作者认为,这包括两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一是使学生在做人做事、待人处世、服务社会方面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二是使学生为进一步深造、追求更高学问或技艺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有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合作与努力。学生应当是教学中的主体,教师是引导。因为教育终究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教育的目标是学生自身精神、文化素质的提升。作者最喜欢引用的名言,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教育使人成为人。”前一个“人”,是自然的不成熟的人;后者则是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的人。通过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反映。作者分析了当前教师与学生中存在的某些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
从学生方面说,当前大学生一般能跟上现代化步伐,思想比较开放、活跃,外语、电脑的掌握和使用能力较强,但独生子女较多,受社会思潮影响较大,心理比较脆弱,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有所缺失,学习上有浮躁或松懈情绪,使用电脑、手机,往往不是用于专业学习,却占去很多时间,因而不能抱定宗旨,专心致志于学业,以至读书少、思考少,不扎实、不深入,为应付考试、获取文凭而学习的,约占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有的学生每天自学时间不到两小时。学数学的不习惯于做习题,学生物、化学的,不认真做实验,学人文学科的,不愿刻苦读经典原著。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牢靠把握,同时也缺乏实践和动手能力的训练。这势必影响提出和分析问题、探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从教师方面说,一般能恪尽职守,认真教学,而且信息来源广,敏于思考。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往往名利观念重,习惯于把科研成果看作“硬指标”,孜孜以求;把教学质量看作“软任务”,淡然处之。不少人热衷于报项目,争课题,获奖项,评“名师”。对教学,则满足于完成工作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课堂上“注水入瓶”的方式,长期以来未能扭转。更有少数教师的讲稿或PPT课件多年不变,反复使用,“上课照本宣科,下课扭头便走”的现象并不少见。
其实,在教学中,学生固然是主体,教师依然是关键(或曰“引导”)。作者指出,常言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没教好的教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谆谆善诱,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本是教师的天职。要尽好这份天职,教师本人必须有真才实学,真有探究学问的兴趣,并且善于引发学生的兴趣。这也正是蔡元培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保证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当前教师与学生中的某些观念和学风必须有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从学校领导方面说,作者主要提出以下建设性意见:
第一,依据本身条件,办出自己的特色。由于趋同化倾向较为严重,一般模仿综合研究型大学,“工往理靠”,文科求全求多,外语、计算机、法律、财经、金融等学科和专业,成为时尚热门,原来具有特色的学校或专业逐渐消失或淡化。其实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高等院校的类型和性质也应当是多样性的。几种基本类型中,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某种分工而已。各类学校应当依据时代的要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或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还有受惠者(包括本人和家长)的某些具体需求,以及校内师资力量、物质设备等条件,来确定学校的类型、性质,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及具体的培养目标,并据此办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形式多样、色彩缤纷、生动活泼、各显其能的局面,才能涌现出学术领域中顶尖级的研究型人才,和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应用型人才。
第二,倡导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对师生要严格要求,在勤奋、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力争创新。对教师不是鼓励争项目、争奖励、争“名师”,而是刻苦治学,探求真理,关爱学生。考评教师的标准,主要不是项目和文章的数量,而是真正的学识、优良的品格、与学生的关系,决不允许浮躁、松垮,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得以蔓延。在论文评审、论文答辩、课程考试、项目申报等活动中,一定要严格把关,以学术水平、学术原则为准,决不允许讲人情、拉关系,滋长不正之风。
第三,酿成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校提供的学术环境与舞台,应当是宽松、自由、平等的,让学生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个性优势。在教学和学术领域,允许学生自由、平等地展开不同观点的讨论与争辩,让受批评者有反驳的权利与空间。这正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不二法门。也是蔡元培在北大开创的一个基本传统。正如作者所说:“历史证明,没有任何‘圣人’能给人才的成长规划出一条具体道路,凭借天赋,打好基础,在实践中锤炼能力,在千变万化的机遇中正确选择,主动、积极、自信地奋斗。这就是成才的条件。大学要出人才,无非是给人提供这样的成长舞台、环境和条件。”[4]
在这里,给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余地是重要的。在重新选择专业上,作者以一系列名人、大师为例。比如钱学森,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留学名额(利用庚子赔款),原来的专业是“铁道机械”,那时清华物理系主任是叶企荪,他了解钱学森的基础扎实,建议他改学航空航天专业,让他先在清华补习航空基础科目,晚去美国一年,后来便成为空气动力学和控制论领域的大师。又如杨振宁,从西南联大考取教育部公费留美项目,原定专业为“高电压实验”。导师王竹溪和赵忠尧联合给教育部写信,要求改专业为“原子核理论。”作者指出:“要是没有这种改变,钱学森会成为导弹卫星的科学大师么?杨振宁能获得诺贝尔奖吗?”[5]可见学校和院系专业领域的领导,应当善于发现和爱惜人才,尽量给他们提供选择或改变专业方向的机会,促使人才的良性发展。
2009年之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入才?)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作者在这方面的许多分析,也算是一种回答。同时作者多次指出:大学里的学习,特别是本科生阶段的学习,主要是打基础,进行基本训练,是不可能直接出现杰出人才的。这需要经过一个毕业后长期的创造性研究,经历反复实践和种种困难与挫折的磨炼,杰出人才方能水到渠成地脱颖而出。但这个打基础的阶段又的确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杰出人才的成长与出现,因而是决不可掉以轻心、漠然置之的。
作者简介:张翼星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参考文献:
[1]王义遒.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2.
[2][3][4][5]王义遒.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71,521,437,384.